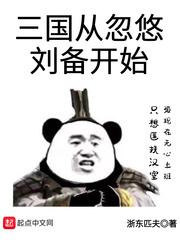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风拂槛露华浓 > 第51章 趵突泉(第1页)
第51章 趵突泉(第1页)
u0006u0015宋辙难过是心疼佑儿,同时也为自己的处境感慨。
这阵子玉京传了消息来,内阁竟调汤玉入京任光禄寺少卿,如今汝州知府空缺,大抵是要由同知顶上。
汤玉自然喜不自胜,虽是同级但一个是京官一个是地方府台,且光禄寺掌祭祀宴享等事务,采买人情油水充足又体面。
刘家在中秋夜丢了百万银两,此举自然不仅是敲打刘氏兄弟,也是给最近官场里摇摆不定的人树威。
下午难得云散,料想是没有再落雨得迹象,宋辙瞥见外头盛开的金菊,搁下手上的奏疏。
情绪在半空悬浮着,看了眼对面书案坐着的佑儿,佯装随意道:“听说有人趵突泉办了赏菊会,随我去走走?”
这阵子衙门事忙,佑儿暂订了孙书吏的缺,就在书吏帮忙理账。
可宋辙却叫佑儿将账册搬到他的公房理,还说是书吏房来往人多,她是女儿家自然要避避。
佑儿还甚是不解,她往日还要抛头露面卖茶水饮子,如今这又算得了什么?
倒是宋辙义正言辞,说是衙门里不比外头,必要严谨些。
说这话时,王书吏休沐在家,还陡然打了个喷嚏。
秋日是济南府最舒爽的时节,远处山峦叠嶂起伏,薄雾之中添了几处明暗交错的橘黄,自成风流。
趵突泉附近已然姹紫嫣红,翠绿垂柳在花瓣上拂过,泉中锦鲤跃然跳起,又逗得周遭游人起了笑意。
自到了济南,佑儿就整日待在衙门里,甚少出门来,更是从未到此来过,此时见景色宜人,渲染出了笑脸来:“竟不知这世上还有这么多颜色的菊花。”
水平如镜,照得人心里也敞亮了。
“你若是喜欢,明日就让人采买些放在后院。”
宋辙这人时而抠搜,时而大方,倒叫人难猜。
佑儿摇了摇头:“咱们衙门谁是种花的料?”
宋辙伸手虚扶在她腰间,挡住了接踵而至的人群,好容易寻了处安静的地方坐下,这才郑重其事道:“你娘的事,我是有责任,这点我不推脱狡辩。
我知你嘴上不说,但心里必然也为她难过,因此我不求你原谅,只求你早日放下此事。”
他在安慰佑儿时恳切真诚,却全然忘了这十来年,自己何尝走出那年家破人亡的阴影。
佑儿被他这般盯着,微微不自在侧了身:“奴婢并未记恨大人,我虽为她难过,却不是因为大人。
她这生刻薄市侩,为了几文银子,不要脸皮去骂去打,却都是想着供儿子读书,可这世上读书人那么多,秀才举人能有几个,更不说中进士的,郑光宗哪里是读书的料……”
佑儿握住拂面而来的柳条,轻飘飘道:“她不过是心疼他,不想自己的儿子成低贱商贾,非要让他高人一等罢了。”
父母之爱子,向来是如此的。
“可她辛苦半生,竟然是这等结局,丈夫和儿子共谋她的性命,大人说值不值得?”
不等宋辙回答,佑儿叹息道:“她这辈子连金簪子都还没戴过呢,记得有一年,隔壁婶子买了根素银簪,她瞧着可好生羡慕,我那时就想给她也买一根,兴许她高兴就不会打我了。”
“谁知我拿了摊上的钱给她买来,她却把我吊起来打,饿了我好几天。”
宋辙看着她松开的柳枝,问道:“那银簪子呢?”
“她拿去退了……”
宋辙生来耕读世家,父母有爱和睦,家里富裕不缺衣食,那种难能可贵的幸福,在这冰冷世道里,就如梦幻泡影,让人惴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