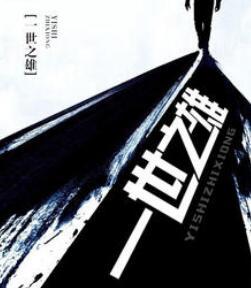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寡嫂是什么意思 > 第五十四章 钱氏的打算(第1页)
第五十四章 钱氏的打算(第1页)
酒过三巡苏贵平姗姗来迟。钱氏激动的伸着油腻手掌,拉他到身边空位坐下。
“贵平……我的乖儿……快叫娘看看,可清瘦了。”
苏贵平有些露怯,一一喊过桌上众人,才对苏大山道:“爹娘何时来的。路途甚远,待我再过几日领了月钱,便好归家看望你们。”
“听大郎说你现下在衙内领职,虽则是个更夫,也需尽心尽力办事,莫要惹出麻烦来。”
苏贵平喏喏应“是”,自顾埋头吃菜。
原本闲适懒散的性子,被揪正不少,苏大山满是欣慰。他倒了一杯酒,举向武怀安,“这小子叫我同他娘惯坏了,若非大郎关照,日后指不定做出什么祸事来。”
武怀安正了正神色,亦举杯,“些微小事,不敢当。”
钱氏听儿子现下做更夫,本就不大高兴,几次三番想开口,让武怀安帮着再安个轻省的,皆被苏大山瞪了回去。眼下开了头,她抢过话来,“不说更夫不好,只贵平年岁尚小,夜里不干不净的东西甚多,我总归是不大放心的。一事不劳烦二主,大郎再看看,衙里没有没较为轻省些的活计,不拘什么,只叫他不成日往外头跑的,都行。”
苏大山也有意儿子找个体面的,钱氏既说出了口,他再打断也无济于事。保不准,真能叫她闹来个好的。
武怀安慢条撕理的挟了筷酸汤鱼吃,咽尽了才回,“年岁稍差些,其他的够不上。哦…对了,”顿了顿,“衙里缺个洒扫搬重的,应当合适。既无夜路行,也不叫日头晒,只待明日卯时巡完便去。”
“不……不……这个好,还是更夫好。”
钱氏悻悻缩在坐上,连带碗里的肉,也尝不出香味。
桌上气氛有些沉闷,武怀安挂着脸吃酒,一时倒没人再说话。
忠叔拎了酒坛子打圆场,苏大山面前空了的杯盅再次满上,“先前见过老太爷两回,亲家彼时不过二出头,现今也生华发。”
苏大山忙双手接下,呵呵笑道:“犹记得那时阿爹身陷囹圄,全拖赖亲家施以援手,不然,我爹哪能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
事经追溯,苏老太爷在世时,靠着一手做豆腐的好本事,在县里小有名气。不是什么贵重的食材,却也讲求个色香味。苏老太爷更是其中好手,各家争相购买。
买卖火红,自有人嫉妒,趁着没人看顾的空档,投了不好的东西进豆腐里栽赃。虽未弄了人命,却也叫那人大病了一场。多年攒的银钱赔光了不说,还被一纸官司,告到了衙里。
千万声‘冤枉’喊破了喉,也无一人相信。只有武青山,怜他贫苦,多番奔走,才将事情始末查明,还苏家公道。
“原以为,定下的会是……”话到一半,苏大山闭了嘴。又见左侧的武怀安微微后仰着脖劲,目光凌厉的扫来。他便知,未尽的话,只能烂在肚子里。
武二疑惑地看了他二人几眼,又把目光带回苏春娘身上。见其神思游离,直盯着他面前的酒盅发愣。
“你也喝一杯?”他端过手边的菊花酒,倒了浅浅半杯推去,“尝尝,口感清淡不大醉人,甘香得很。”
“你说……”苏春娘心里有个小小的疑惑,她凝视着身边武二,只看得他浑身不自在。
“什么事?”
“没有。”她摇摇头,顺着他的手,将那杯菊花酒喝尽。烈酒独有的辛辣,即使加了再多的糖,也掩盖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