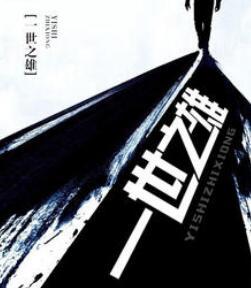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寡嫂是什么意思 > 第四十九章 流言四起(第1页)
第四十九章 流言四起(第1页)
一去便是两个时辰,再归来时,绣娘们下了工,铺子里只剩苏春娘一人在。
“婶子可问明白了?”
张娘子倒了杯冷茶,几口灌下,方说道:“那蠢妇到处宣扬我们铺子同望春楼有牵连。”世人对青楼女子的成见向来颇深,又怎会与她们用同一个地方出的物件。
十几件衣裳正在赶制,这是实情,无处伸辩。若因此事上门寻衅,反坐实了他们心里有鬼。
张娘子气得头顶冒火,站在门前指桑骂槐说了一通,心里才舒服些。
“行了,明日事明日再操心,先将手头的解决了。”
收了铺,关了门,苏春娘与张娘子一道归家。一路上,两人思量多回。生意才将将起步,虽说不需租金,人工成本却日日都在增加。苏春娘更是将手里头的银子花了七七八八,正等大展拳脚,又出了这等子事。
“若不然,咱将铺子里的小件儿,都匀了给货郎兜售。走远些,流言蜚语便这不到这上头来。”
张娘子一想也行,那批衣裳要得紧,现下没空闲管旁的。
“你做主就成,总归是你相熟的。”见苏春娘始终恹恹的,宽解道:“货好不愁卖,眼下困境只是一时的,久了他们自然就忘了。”
一室烟火气,一桌四人五碗食,吃罢各自回了房。
苏春娘拾掇了杯碗进灶间,冰水沁凉,如覆了冰。她面不改色地甩去指间还滴落的水,回头正瞧武怀安倚在门框子上,不知看了多久。
“大伯可是要热水,我现下就烧来。”
武怀安不应,自顾自说了另一件的事,“如今河塘上冻,泥沙挖不成了,不若送你阿弟去开矿?”
“……”那是惩戒犯了事的罪犯才去的地方吧。
苏春娘暗自腹诽,直勾勾地瞪过去。此时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表达的意思直白又干脆,她不同意。
武怀安搔搔额角,不耐烦的‘啧’了声,道出的话,偏多了分局促的尴尬,“是重了些,容我再想想,寻个轻省的活计安排他去。”
摒着的面庞总算开了颜,不管叫苏贵平做什么,武怀安也要顾及到她的脸。
苏春娘勾了唇,妍丽的五官陡然舒展开,真诚道:“全凭大伯的意思。我阿弟自小受尽疼爱,合该吃些苦头的。”
武怀安点头认同,男人哪能怕吃苦,像苏贵平这样的软脚虾,他有心磨一磨。
“打更的老张头前儿卸了职,正好喊他去试试。”
更夫是个不错的差职,不需花死力气。天黑走到天亮,敲敲梆子,打打锣,熬一熬就过去了。且晚间也有巡街的差役,苏春娘很是放心。
“在此谢过大伯为我阿弟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