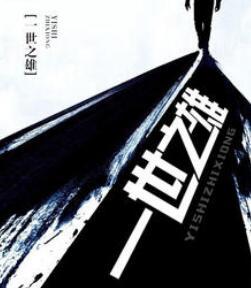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寡嫂是什么意思 > 第二十八章 心生埋怨争相对(第1页)
第二十八章 心生埋怨争相对(第1页)
苏春娘哆哆嗦嗦抿嘴呜咽,也猜出这人约莫正是伤了武二郎的罪魁祸首,他才会如此意决。
任他再侠义热肠的人,家仇在前,左右逃不去不相干几字。她心头闷苦,竟真阖了眼存下死志。
汉子眼波滚动,转辗两人之间。他面貌粗陋,内里恰恰缜密如发。苏春娘面上,他不必看,除了惧怕惊恐必不无其他。再看武怀安面上,颇耐人寻味些。他有心查验一二,是以手里动作刻意加重几分。
苏春娘面上神情骤痛,口中断断续续传来难忍的低、吟,武怀安出声制止,竟要同他谈起条件来。
“不妨这样。你放了她,我容你缓上一刻。之后……活命还是下牢,端看你自家本事,如何?”
匪贼嗤嗤笑道,“装腔作势,诓人瞒骗乃我看家本领,你二人自有干系在,我无意探究。有她在手,还怕逃脱不去。这样,你现在招人返去,我带她走过五里坡外,再将她放了。”
武怀安不再言语,握在刀柄处的手,越发紧切。他浑身蓄力,警惕的觑着匪首松懈的空档,誓要一击击中。
如果真伤及性命……他压下蓦然冒出来的念头,谁人的性命不是命,再薄情的爹娘也有怜子之心。
他心里已妥协,嘴上却反对,“我说了,今日既碰上你,万没有眼睁睁看你挣脱的可能。我只给你半刻,是走,还是留。”
男人一咬牙,心里有了计较。论此处深浅,再没人有他熟悉。左右避着荒路走,难保还能看出他走的哪条道。
“你的话可真?”
武怀安龇牙谩笑,“莫道谁个都是你。”他需把人交给小吴他们,才能放手去搏。
那头两个贼人尚未昏去,僵起半身,脱口骂来,“好你个卑鄙贼子,连你亲爷爷也诓。”
男子略有不赞同,好心教他们一课。
“你同个强匪谈什么信用,老子自来刀尖舔血过来的,还能怕你不成。待你们有的命出来再论别个。”
重要的跑脱了,留下的没甚用处。再心有不甘,小吴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贼首消失在视线中。
武怀安比之先前逾发忙碌,一连几日审问抓来的四人。重刑都用上了,仍没挖出几句有用的。
狡兔三窟,那贼首虽与他们同吃住,劫来的银钱却不说多拿一份,也从来不跟人交心。他自哪里来,家里还有几人,他们一问三不知。
也只其中一人,自他头回犯事便跟在身后,知他有一个相好的,却不晓得安在何处。每劫下一桩货来,会寻几日过去一回。他们也没那等细腻心思,想着跟去拿捏他的把柄在手里。
劫货杀人,死罪是逃不脱的。武怀安受令押了几人去往府城受审,哪知衙府案卷之内,自有他们姓命在。光杀人事件,就成五六起之多。更遑论劫财伤人。无需复审,自判了几人秋后斩立决。
此行不光弄清匪首姓甚名谁,老家何处,却还有意外之喜。武怀安点点案档上头,那张潦草的人面相,讥讽意味深浓,“周守义……”
秋意起,院里的榆树梢头零零丁丁挂着几丛枯色。树阴下,避着两抹身影,一坐一躺。
武二摊手摊脚的仰在腾椅里,半副身子叫日头晒得热烫,他微敛着眼,看正在树下制衣的苏春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