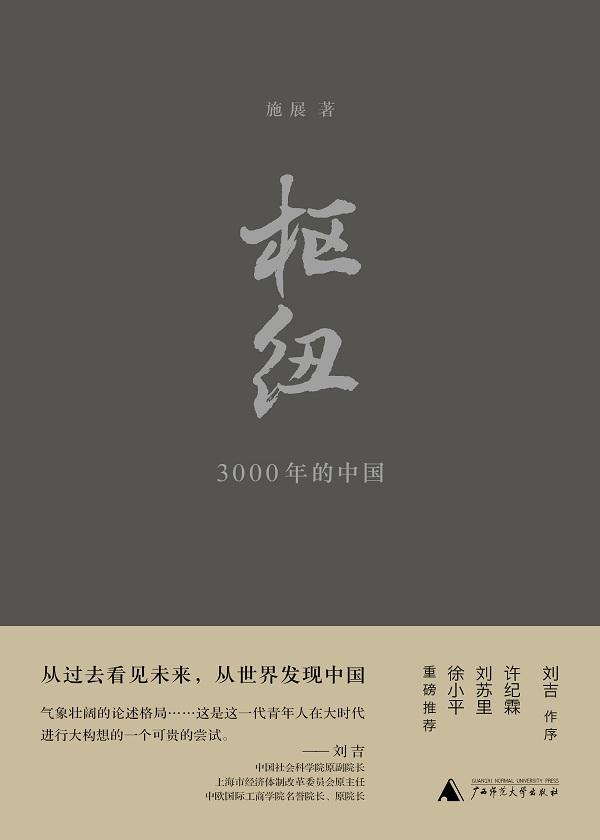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地椒花是什么 > 薄 雪(第2页)
薄 雪(第2页)
缠香急忙过来说:“妈,你不敢动,让我看。”脱下婆婆的裤子,婆婆果然拉在了裤子里,臭味逼得人不敢喘气。缠香用纸擦干净,再用湿毛巾给婆婆擦干净腿,重新换了干净裤子。屎裤子要用外面的土抹干净,再用水洗,这样看着不那么恶心,还能节省点儿水。每一次挑水缠香都累得浑身像散了架。有时她真想让那些臭烘烘的脏衣服就那样堆着,不理它们,但她又有些不忍心那样做。她心想,要是能下一场雪就好了。缠香心里盼着下雪,盼了很长时间。缠香想下了雪,收了雪水,就不用去沟底挑水了。终于,老天爷遂了缠香的愿,没过几天山里降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缠香早晨推开门一看,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雪是在夜里悄悄下的,而且还很厚,这下能往水窖收雪了。缠香在外面兴奋地忙碌着,雪厚,扫帚扫不动,就用木锨铲。缠香把院子里、硷畔上、坡下的雪全铲一块堆起来,拍瓷实,每一堆雪中间挖一个眼儿。这样等雪冻成冰坨,从地下铲起,用一根粗绳子穿进眼儿里,将这个冰坨子拉到水窖旁,用铁锨铲成几块掀进水窖里。一进窖里,窖里的温度比地面高,用不了几天冰坨子就融化成水了,这样省工又省力。
喜鹊来问她借木锨,神秘地对她说:“有新鲜事呢,知道不?”“啥新鲜事?”喜鹊凑到缠香耳旁低声说:“二喜婆姨小桃怀孕了。”“这有啥稀罕的!”“你知道她男人是啥时走的?”喜鹊瞪着眼看着缠香,“他男人半年前就打工走了,一直没回来,孩子从哪里来的?”“你咋知道?”“前两天我去沟里挑水,见小桃挑着两大铁桶水拼命走着,也不歇,汗珠子像雨点一样。走不了多久,就放下水桶呕吐一阵,眼泪鼻涕糊一脸。”“那也不一定是怀孕,说不定是着凉了。”“嘁,那种事逃不过我的眼睛。”“是谁作的孽?”“还能有谁。”喜鹊撇撇嘴。“这可咋办,他男人回来咋交代?”“谁知道,等着看好戏吧!”“你不敢向外乱说了。”“我知道。”喜鹊扛着木锨走了。缠香望着远处的皑皑白雪发了很长时间呆,她感到彻骨的冷。
缠香在院子里放着两个大黑缸、两个大黑瓷盆,为的是多收些雨水或雪水,现在都盛着满满的雪。雪消融后,缠香就用雪水给婆婆洗屎裤子。她死劲儿揉搓着,洗了几遍,可那股子臭味总是洗不掉。雪融化后的水冰冷刺骨,缠香的双手都失去了知觉,手指惨白,没有一丝血色。缠香舍不得热水,没有烧的东西,节省下来还要给婆婆做吃的用呢。
窑里冷,婆婆不停地咳嗽。缠香知道这场雪下得又带来了新麻烦,水不用挑了,可烧的东西又成了问题。外面的一切都被雪压了,粪也拾不成,庄稼秸秆所剩无几。再说庄稼秸秆又不耐烧,没有火力,燃起来火苗看着很大,但很快就熄灭了。
缠香看着燃起来的火苗在几分钟内熄了,就幻想着能有几块炭就好了,可以燃很长时间呢。但这大山里就是有钱买炭也拉不回来,交通不便,架子车到不了尖山村。看着那细瘦的羊肠小道,缠香不明白,老祖宗怎么把家安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年腊月二十五,富生打工回来了,身后背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不知装些啥,看上去鼓鼓囊囊的,把富生压得大冬天背上的汗浸透了棉袄。村里人都不知富生背回了什么宝贝,都稀罕地撵到家里来看。富生将他们统统撵出去,不让他们看,一脸的神秘。缠香也兴奋好奇地看着富生,究竟是什么东西?当富生慢腾腾地解开裹了两层的蛇皮袋子,原来他背回来了几块炭。
看着乌黑发亮的炭,缠香眼里顿时涌出了泪水。她心疼地说:“你傻吗?一百多里路,背回来几块炭!这煤疙瘩多沉啊!”
富生咧嘴一笑说:“你不是想有炭烧吗?”缠香每次想起这件事,都会偷偷地笑起来,心里暖暖的。富生是疼她的。
一场大雪使这户人家陷入了困境。没有烧的,缠香想她年轻可以抵抗寒冷,婆婆却不行。眼看着婆婆混浊的眼睛睁得像牛眼似的,那眼球似乎都要蹦出眼眶。婆婆一口一口在那里费力喘气,缠香心里很难受。家里所有的庄稼秸秆和平时攒下的牲畜粪所剩无几,再也没有什么可烧的了。前几天喜鹊给了她一背篓羊粪,喜鹊家也缺烧的,不好意思再向人家要了。
缠香想到了村里羊圈里的羊粪。自包产到户后,本来队里集体的羊也应分到各家各户去,但没有分,村主任不分。村委会没有钱,村主任说还要靠这群羊每年卖羊绒的收入供村委会的日常开支呢。原来老村主任活着时,村里人没烧的,村上规定各家轮着在村里的羊圈里扫羊粪。今天你扫,明天他扫,很公平。这样轮了很多年,相安无事。老村主任患病去世后,新村主任就打破了原来的规定,不让轮着扫了。说没有烧的困难户给适当解决,有烧的就不给了,攒下羊粪村委会要种地用。
也就是说,村主任让谁扫谁才能扫。
村里的羊圈围墙很高,村主任怕人偷羊粪,专门给羊圈焊了个铁栏杆大门。羊在不在圈里都会锁着大门,谁也进不去,别说偷羊粪了。要是没有下雪,缠香也不至于这么窘迫,山坡沟坬总能搂些杂草和牲畜粪便。可现在地上铺着厚厚的雪,天冷一时消不了,到哪里去找烧的呢?缠香来到村里的羊圈旁,见大铁门上挂着锁,放羊的把羊赶出去了。这么大的雪,羊出去吃什么呢?缠香透过铁栏杆向里望去,见羊棚底下羊粪堆得很厚。棚子外面的羊粪被雪压了,羊踩踏后羊粪和雪搅混起来。
一股浓浓的粪味扑鼻而来。不知为什么,缠香闻着这熟悉的羊粪味,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臭,反而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在心里蔓延。那些和雪搅混在一起的羊粪,就像一颗颗黑珍珠掺进白面粉里,那么耀眼、好看。她真想进到羊棚里揽上一背篓干羊粪,回家把炕烧得热热的,这样婆婆就不会受罪了。
缠香在羊圈外面呆站了很久。她犹豫着,最后决定去找村主任。她估摸着这个时间村主任在家,他老婆肯定也在。缠香不明白,村主任婆姨是个有名的醋坛子,平时盯村主任盯得很紧,但村主任还是想干什么就干。村主任正坐在桌前一个人玩扑克牌算命,面前放着一盘炒花生米。看见缠香,他有些惊讶。
村主任窑里暖烘烘的,一股煨羊粪的味道。村主任婆姨正在做饭,看见缠香,只淡淡地招呼了她一声,就低头做自己的事,也不招呼缠香坐。村主任冷冷地问:“你来做什么?”缠香说:“我婆婆气管炎犯了,家里太冷,没烧的,求主任同意在村里的羊圈揽点儿羊粪。”“嘿嘿,你也求我?平时帮你你都不要,这次需要了?”村主任回头瞥了老婆一眼。他老婆狠狠地瞪了村主任一眼,同时也瞪了缠香一眼。村主任婆姨虽然在那里做着饭,但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村主任的监视。村主任对着缠香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早就给你说嘛,男人不在家,女人要有个依靠。想要羊粪,等村里研究一下,给你回话。”缠香转身出了门,她知道村主任在找借口,揽羊粪这点儿屁事,还用研究?
大雪地里,二奶奶穿着那件破旧的黑布棉袄赤着脚追着她们姐妹要糖吃。她们哪里有糖,为了逗二奶奶,就把雪捏成一个小圆球用纸包成糖球样,递在二奶奶伸到她们面前的那又黑又脏的手里。二奶奶急切地剥开纸,一口把雪球吃进嘴里。
她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手指着二奶奶喊道:“傻灰婆!傻灰婆!”二奶奶憨憨地对着她们笑。缠香突然笑醒来,原来做了个梦,梦里回到了童年。
缠香裹紧被子,再无睡意。冬天的夜太漫长了,由于窑里寒冷,更加难熬。她想起白天找村主任的事。本来不能找村主任,缠香知道,但没有别的法子。如果自己也被村主任欺负了,像小桃那样怀了孕咋办?缠香越想脸越烧,心也扑通扑通乱跳起来。她捏了一把自己发烧的脸,悄悄骂自己,你胡想些啥?
这么不害臊!也许富生离开太久,她想富生了。她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出事,要不怎么对得起富生。
想起富生,缠香眼泪就流了出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睡呢?是睡在寒冷的工棚里,还是在廉价的出租房里?吃得饱不饱?缠香想着一阵心酸,富生在外面为了挣几个钱,多不容易。
她在家也受罪,要不是婆婆,她一定撵着富生去了,两个人在一起再苦再累,心也是踏实的。她心里这么酸一阵苦一阵,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突然,缠香感觉身边的婆婆怎么连一点儿声响都没有。平时婆婆睡觉不是有很重的呼噜声,就是有吃力的喘气声。她慌忙爬起来,手放在婆婆鼻子底下,感觉到了婆婆的呼吸,才松了口气。黑暗中,缠香把压在婆婆身上的老羊皮袄往上拽了拽。
睡不着,缠香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
她和二姐缠定在山坡上放羊,二奶奶像尾巴似的跟在后面。
“缠香,给我吃个糖。”二奶奶手伸得长长的,问她要糖吃。
她装模作样地在兜里掏着,可掏了半天也没有,便在二奶奶面前展开空空的两只手。二奶奶失望的表情令她不忍。二奶奶年轻时生过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一个也没留住。最后在四十二岁那年又生下个儿子,不知怎么疼才好。夫妻俩生怕孩子再有个什么闪失,但那孩子在五岁那年还是没有留住,患急性脑膜炎去了。二奶奶也因此落下了病根,精神不正常了。整天疯疯癫癫,只知道把破衣服或枕头填进衣服里,把肚子隆得高高的,逢人便说她又怀孕了。还有就是不论看见谁家的孩子,二奶奶都会尾随在人家屁股后面。她和二姐出去放羊时,二奶奶就经常跟着,眼瞅着她俩蹦蹦跳跳的样子,二奶奶的脸上就会浮起非常安静慈爱的笑容。二奶奶自从变成这个样子后,就有了一个嗜好,爱吃糖,只要看见大人或小孩,不管认识不认识,她都会把手伸到人家面前要糖吃。只要一说“糖”字,她口里的涎水就会不自觉地从嘴角流出,收也收不住,那神情就像一个孩子。“你有糖吗?给我吃个糖。”缠香始终搞不清楚二奶奶为什么那么爱吃糖。听说二爷爷曾经找过算命先生,说二奶奶命里克夫,一辈子无子嗣,所以二爷爷就把一切不如意都归罪于二奶奶,从不关心她,不是打就是骂。二爷爷曾经有过不要二奶奶的想法,要和二奶奶离婚。但那时他们都四十多岁了,二爷爷家穷,不可能再娶个媳妇。二奶奶问别人要糖吃,特别是在陌生人面前要,二爷爷觉得很丢脸,经常打二奶奶。一次缠香亲眼看见二爷爷抓着二奶奶的一只脚,倒拖在地下往回拉,一边狠狠地说:“我拖死你,让你再要糖吃!”二奶奶最终还是奔着甜蜜的世界去了。一次她在垴畔上走着,垴畔边长着一棵杏树,树上结着青杏。她突然兴高采烈地喊叫起来,说那杏树上挂满了糖果,便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摘,结果从垴畔上摔了下去,再没能醒来。
那以后缠香经常梦见二奶奶追着她要糖果吃,有时眼睛一闭,就看见二奶奶可怜兮兮的模样和伸到她面前的那又黑又脏的手,以及嘴里流得长长的一直挂到胸前的涎水。
缠香迷迷糊糊睡着了,又被婆婆的咳嗽声吵醒。她觉得自己困得不行,眼皮都睁不开。旁边的婆婆一声声咳着,缠香揉揉眼睛,慢慢清醒过来。瞅见婆婆咳到换不过气,缠香急忙爬起扳过婆婆让她仰躺着,用手在她胸前使劲儿捋,捋了好一会儿,婆婆的气才顺了些,乌黑的嘴唇渐渐有了血色。“娃,你说我咋不死呢?”婆婆一口口喘着气。“妈,你胡说啥呢!”“我要是死了,也就不会拖累娃了。”“妈,你好好活着,有我呢。”
缠香安慰着婆婆,她给婆婆盖好被子。“没有烧的,这窑里冷,我气憋得上不来。”“妈,没烧的,我会想法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