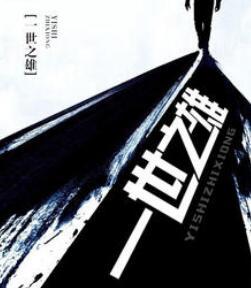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明日方舟rap > 第40章(第1页)
第40章(第1页)
库尔斯克山谷这六公里的宽度是最适合大兵团通过的地形,而在山谷北岭的左右两侧,都是绵延的森林,而且坡度越来越大。
于是,无论是在防线西侧树林展开的步兵第五团,还是在防线东侧树林里待命的骑兵团,都没有遭到实质上的攻击。乌萨斯军队只有一些小股步兵来袭扰。眼见这些山坡上的树林里有子弹射出,就掉头撤走了。只有少量骑兵远远地监视着。
漫长的炮战和汹涌的人海没有波及到树林里的骑兵团。骑兵们只是全副武装地坐在拴马处附近,听着外面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和铺天盖地的枪炮声窃窃私语:
“外面正在打机枪啊……”
“准是在扫射帝国军队……”
而在前沿位置的观察哨上,骑兵团长别尔康斯基和骑兵团政委茹科夫从战斗打响起就一直没有离开过。
别尔康斯基一直在用“前乌萨斯帝国军官”的身份为茹科夫不厌其烦地介绍着面前的战况。从步兵队形到军旗番号,再到各支部队的历史和特点。这其中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团长早就介绍过,被保民军指挥员们烂熟于心的,所以他是在说废话。茹科夫理解对方的举动:安德烈不过是在借此舒缓自己的紧张。
然后别尔康斯基突然主动提起了那件大家都在回避的事情:“我看见了线列步兵第42团的军旗。传说在以前的乌萨斯内战和叛乱里,敌对双方的人都有朋友在对面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您看,一场内战,不论它的性质怎么样,都免不掉这种桥段。”
“我可以当个忠实的听众。”茹科夫只能这么回答。
“我和瓦列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我们原来生活的叛逆者。不过他稍微走在我后面一些。然而慢了一点……就是现在这样,不是我们以前骑着扫帚挥舞木棍打着玩了。”
别尔康斯基看了看旁边的茹科夫:“无产阶级的智慧能为我这样的困境提供什么帮助吗?政委同志?”
“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是,确实没有。”茹科夫稍稍摇头,“我们的理论在于解释政治、经济和历史。主要是帮助人们确定思考的基本路线,而不是像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我只能说两点,首先,随着这场战争以后扩大,这种情况将更加普遍;
“然后,无论如何,我们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要为之负责。我们要在各自的位置上恪尽职守。”
别尔康斯基长长地出了口气:“是的。毕竟我自己选择站在了这边……”
然后两人和周围的骑兵们就被火箭炮的齐射吓愣住了。
把他们从寂静中拉出来的,是背着无线电飞奔过来的通信兵:“团长同志!政委同志!司令部命令,骑兵团进攻!”
下一刻,两人触电般跳起来,翻身冲回部队的隐蔽地,边奔跑边下着命令。不到三分钟,原本以连为单位散在树林里待命的骑兵们已经上马集结,列出一条条横队。
骑兵团的政委挥起了鲜红的团旗。亲自充当旗手的团政委单手擎着红旗,在骑兵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冻原的战斗口号——
“骑兵团!整合运动党员集合——!”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马刀,党员们高喊着抽出了马刀,普通战士也高喊着抽出马刀。
喊过之后,骑兵们又沉默下来。政委小心翼翼地将团旗的旗面卷在旗杆上,将旗杆像骑枪一样夹在腋下;战士们把马刀斜摆在身体侧下方拎着。
别尔康斯基团长亲自抓住团火力营的营长,嘱咐他的机枪马车和迫击炮必须持续保证火力掩护,直到骑兵突入敌军步兵队形之中。
然后,骑兵们开始运动。
从树林里向外运动时,驮兽们迈着缓慢的常步,“嗒嗒嗒嗒”四节拍的动静连贯但微弱,几乎淹没在战场嘈杂的背景噪音中。随着骑兵团的九个骑兵连队全部离开林线,驮兽们开始提速,从常步变为小跑。随着速度提升,驮兽斜对角的两只马蹄同时起落,成了两节拍: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骑兵团的三个营在小跑中完全展开,每个营都以两个连队在前一个连队在后的队形展开,力图最大限度地发扬冲击力,尽管这样会给敌人更大的射击目标。
别尔康斯基开始动作。团长与政委一样,并肩跑在队伍最前面。他一只手紧握着缰绳,一只手上缠着马刀穗子。随着他无声地用马刀向右一指,又向左一指,然后向前一指,在耸起的马耳朵上方斜举。骑兵们的脑子里同时翻译出了这个无声的口令:
全体冲锋!
红色的战旗倏然立起,被大风展开。驮兽们大跑起来,四蹄翻飞,沾地即起,变成了“嗒嗒——嗒”的三拍。
下一秒,骑兵们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高呼:“乌——拉——拉——拉——拉——!”
警戒的乌萨斯骑兵们惊恐地看着从不远处树林里涌出的敌军骑兵扑来。涌动的骑兵横队仿佛从幽暗深海中猛然荡起,起伏着冲向陆地的海啸。乌萨斯骑兵手里的转轮手枪和马刀,握柄汗得像在水里泡过。几乎没做出什么抵抗,他们就开始作鸟兽散:这里不过是个散开警戒,连集合都来不及的骑兵连,敌人却是整整一个团上千名骑兵!
跑得慢的乌萨斯骑兵转眼间消失在骑兵团的洪流之中。他们唯一的意义是为被炮击严重惊吓的乌萨斯步兵第42团争取到微不足道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