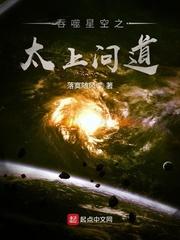笔下文学>废帝与宫女视频讲解 > 第87章(第1页)
第87章(第1页)
徐皇后一走,长信宫便清静下来。欢喜刚巧回来,魏王颔首,问:“你烟姐姐怎么样?”
欢喜道:“换好衣服了,人坐着休息。小的已叫厨房备上驱寒汤了。所幸姐姐也只是在水里随便走了走,不至于伤了身子。”
魏王道:“那可不好说。”
他原本在御书房与初返京城的舅舅说话,话至一半,就有个小太监匆匆来报,说皇后到长信宫找麻烦来了。不等皇上开口,魏王便已自顾自离开了御书房,回了长信宫。一进门,他就见到朝烟在水里头摸索,这才有了前面那一出。
他从来都随着性子做事,早就把阖宫上下得罪遍了,扔一个皇后下水,也算不得什么大事,扔也就扔了。更何况,原本就是这皇后娘娘自个儿找茬。
魏王又等了一会儿,人走到朝烟的耳房前,敲了敲门,问:“朝烟,你好了没?”
“殿下?”屋里头传来了朝烟的声音,“衣服倒是换好了……”
听到这话,魏王便推门进去了。这一进门,就瞧见朝烟脱了鞋坐在床边,一双脚赤着,刚泡过水的脚背肌肤白嫩的发亮,雪莹莹的,很是勾人眼球。他在门口愣了会儿,眼光止不住地往她的脚上飘。
“殿下…”朝烟也木了一下,察觉到他的视线,便紧着把脚塞进布鞋里,下来请安,“殿下怎么进来了?这里粗陋,待不得。”
“粗陋什么?你天天住的地方,我怎么就不能来了?”魏王却不以为意,将门合上了,“不必客气了,坐下休息吧。”
朝烟又坐回床上,但这回不敢脱鞋了,老实把脚安在鞋履中。
“皇后除了叫你下水捞发簪,没做什么其他为难你的事吧?”魏王问。
“……没有。”朝烟摇头,又有些不放心,道,“殿下,您也别将这事儿记在心上。她是皇后娘娘,我是宫女,她叫我去取发簪,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将她扔进了水里,这太不占道义了……”
“便是我不将她扔进水里,也没几个人会夸我正经的!”魏王不以为意。
“那殷将军呢?”朝烟竖起了眉,正色道。
魏王的脸登时僵住了。
舅舅第一天返京,他与舅舅说话说了一半便跑了,回了长信宫,然后将堂堂的一国之母、皇后娘娘扔进了荷花池子里。要是舅舅知道这事儿,怕是得气得又抄着鞋底追着他跑了!
魏王僵硬了片刻,道:“……罢了!舅舅要是当真生气,那就生气吧。能叫徐皇后不欺负你,这也算值了。”
见他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朝烟竟打心底觉得好笑。她不禁问:“值得么?”
——为了给她撑腰,一气儿得罪了皇后,又惹怒了殷将军。这值得么?
魏王郑重了面色,道:“值得。”
朝烟摇了摇头,叹气说:“也不知我哪里来的这么大情面?”
魏王笑了笑:“是老天爷前世给的缘分。”罢了,又道,“我才说过要护着你,这决不能食言的。”
朝烟听他讲胡话,说:“殿下又在开玩笑了。人哪里来的前世?我从前指不准是一株花花草草呢。”
魏王露出神秘之色来,道:“天机不可泄露。”
二人正在说话,外头传来了欢喜的声音:“殿下,何公公来问话了,想问问咱们这儿是怎么了,如何与皇后娘娘冲撞上了?您瞧瞧,怎么回话好?”
闻言,魏王露出了轻微的恼色。他说:“算了,本王亲自去回话吧。”然后,他高挑的身子便站了起来,向着门前去了。要出门时,他回身与朝烟说,“朝烟,这回我可是立了大功。你想想,怎么回报我?”
她愣了愣,心底埋怨:她能给的出什么回报?横竖不过一条宫女的性命罢了。他还想讨要什么呢?
可魏王已经推门出去了,吱呀一声响,门就合上了。
朝烟叹口气,想起徐皇后那盛气凌人的样子,登时替魏王觉得不值。
她朝烟也不是什么要紧人物,他如何做出这样绝情的事来?将徐皇后直接扔下水,解气倒是解气,料想皇后日后也没胆子再找她麻烦;可这样做,弊处远大于利处。
且这样的账,她要如何还呢?
朝烟静默片刻,人走到了桌案前。她研开了墨,又抄起笔,人思虑一番,手竟然不自觉地动了起来,在纸上写写划划。待她回过神来,竟察觉到自己在纸上抄了一句古人的诗歌——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墨迹绵延隽秀,正是属于她的字迹。
朝烟愣愣地看着几列字,脸莫名有点发烫:她怎么写了这么一首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