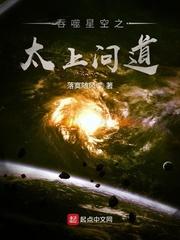笔下文学>漂亮朋友实体书番外图片 > 第36章(第2页)
第36章(第2页)
李殊碰不到沈宜游的手,觉得他们隔得未免太远,试了几下,把扶手收起来了,然后伸出手,松松地捉住沈宜游的手心。
沈宜游的手很软,也很滑,手指细长。
李殊握在手中,心中立即产生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
因为这是从七月份发脾气开始,沈宜游第一次完全没有拒绝李殊。
沈宜游很轻地笑了笑,与李殊对视着,又抬头看了一眼前座的司机,凑近了李殊,轻声说:“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呢?”
“最近要回湾区吗,”他问,“还是一直等到上市结束?”
他告诉李殊:“我这次不能留太久,最多一周,就要回去了。”
沈宜游的嘴唇颜色像李殊童年时期在祖母的花园中种植的大马士革蔷薇,在张合时轻微颤动,唇间露出的牙齿洁白,跳动的舌尖则是鲜红的。
沈宜游问了一堆问题,认真地等待李殊的回答,过了一会儿什么都没等到,稍显困惑地眨眼问李殊:“你在听吗?”
李殊确实不在听,所以也没有说话,他靠近沈宜游少许,吻住了眼前柔软湿润的,轻盈甜蜜的嘴唇。
这实际上是几天前,李殊走近S市的日本餐馆,准备给沈宜游打电话时在心里想的事。
那天李殊拿着手机,得意地想,虽然自己不是真的每天都很空,而且总是惹沈宜游生气,但今天应该能够得到沈宜游的一个吻。
因为三年前他突然出现后,沈宜游第一次吻了他。
(五月九号,上午七点零八分。)
不过很快,因为一些李殊不愿再提的原因,期待很快dàng然无存,李殊也没有拨打沈宜游的号码。
幸好,没过多久,李殊还是得到了这个吻。
也许是因为前座有司机和艾琳,沈宜游眼睫低垂着,没吻多久,就向后让了让,用很轻的声音说:“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沈宜游面颊微红,好像有一些羞涩,像一颗覆着晨雾凝成的露水的,新鲜采摘的樱桃。
他们的双唇也还胶着着,没有彻底分开。
李殊说“不好”,说“不要”,含混地叫沈宜游的名字,按紧了他的的腰,吮吻他的唇舌,沈宜游便妥协了,重新贴近了一些,顺从地与李殊吻得难舍难分。
不过很快,李殊的律师打来了电话。李殊只能放开了沈宜游,但仍然牢牢攥着沈宜游的手,和律师通了简短的话,确认了四十分钟后,在酒店房间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