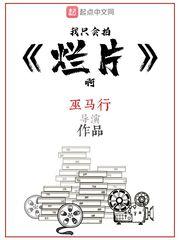笔下文学>夜来香花期有多久一年开几次 > 第一百五十五章 滂沱(第3页)
第一百五十五章 滂沱(第3页)
何曼很少吃这个,她早前过得糊涂,也玩儿得很疯,两次流产手术没做好,后来她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收敛了不少,接活动时都有了条件,不是随随便便那种。我估计这么久以来除了杜老板那伙人硬来,她几乎没再吃过,看来那男孩这段时间一直住这里,何曼也挺傻的,撕裂的伤还没痊愈就陪着那男孩,大小伙子没轻没重,她可真够豁得出去。
其实这行女人比一般女人都傻,稍微有点爱情甜头尝,就不管不顾的一头扎进去,在那种场所过久了,特别渴望有个男人疼一疼宠一宠,所以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都不想放过。
何曼洗了澡我给她涂药膏,她身上伤不重,都是外伤,岚姐去厨房熬了点粥,她说不饿,也不吵不闹,就安安静静坐着,她脸上有笑容,表情很轻松,可透着空洞。
岚姐没待太久,她男人给她打电话,说买了一辆新车送她,让她回去试着开看还顺手吗。
何曼坐在床上吸了吸鼻子说好羡慕啊,岚姐说羡慕个屁,她老公买的车不是黑的就是灰的,她越开越觉得自己老了,老男人就是没品位,以为她喜欢那些死气沉沉的颜色,守旧又古板。
她虽然这样啐骂着,可眼睛里都是蜜意和欢喜。
岚姐离开后何曼的脸彻底垮下来,她叫了我一声,我问她怎么了,她问我有没有看到岚姐脸上多了什么。
我没有说话,她撩了撩自己湿漉漉的头发,“光彩,一种被男人呵护着的光彩,是女人依靠自己怎么拼都拼不来的。”
她说完看着我,“你脸上也没有。原先还有过一阵,后来就彻底不见了。”
我垂下眼眸沉默,她笑了笑,“很可悲。有些路一旦踩上去,很难再回头,社会并不是给所有人重新来过的机会。我和江北的合同还有一个月到期,我没打算再干下去,我就想和他好好在一起,恨不得把心和肺都掏出来给他。他特别好,你对他有偏见,他真的很简单,就像温水一样,他不会过分冰凉伤到我,也不会过分灼热烫到我,他给我做鸡蛋面,牵着我手逛市场,你也许觉得很可笑,你穷怕了,没钱没本事的男人你看都不愿意看,但我不是,他给我的东西虽然平淡可让我放不下。我和他在一起十三天,这是我活到现在最好的时光,我从没想过结束,如果不是今天的事,我想我永远不会和他结束。”
她发现我对于这份好笑的告白无动于衷,根本没有把这认为是爱情,早不是祖辈父辈的纯真年代了,现世贫穷的人生存倘若都困难,拿什么去喂养爱情这只贪婪的魔鬼。
她不再和我诉苦,而是盯着窗子上一滴滴打落的雨珠,那些雨珠起初只是偶尔才掉下来一滴,后来变得越来越密集,很快将玻璃染花,氤氲开一圈又一圈模糊的水纹。
她喉咙哽咽着,“下雨了。”
这是一场酝酿了很多天的大雨,外面唰唰的声响,伴随着霹雷和狂风,天地间陷入混沌。
我爬上床将玻璃推开,夹杂着青草气息的濡湿空气扑面而来,狠狠的砸着皮肤,暴雨倾盆而下,闪电由南向北劈得凶猛,一棵大树早已轰然倒塌,漆黑的天际一团团灰暗的翻滚的云层,沉甸甸的倾压下来,犹如一只血盆大口。
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正和狂风顽抗,不仅寸步难行,而且几乎要被卷到空中,他们死命扒住一块墙角或者树干,我听到隐约的哀嚎声呼救声,就像真的世界末日。
滨城这几年也没有过这么大的雨。
像要把整座城市都吞噬和湮没。
我注视着这样的滂沱大雨,“还有很多时间,会遇到更好的,着急得到的都是将就的。”
她嗯了声。
这场雨瓢泼大雨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地面全部是积水,一半井盖被堵住,低洼的坑处犹如一片泛滥的湖泊。
雨小了一点时,何曼催促我回去,我不放心她自己,她说难道还要盯她一辈子吗,她不至于那么想不开,否则她也活不到现在。
我拥抱她安抚了两句,她让我帮她向岚姐请假,想去看看海,也许能忘掉很多。
我问她回来能见到我从前认识的那个何曼吗。
她说一定。
说的时候笑中带泪让人心疼。
我从公寓出来,透过尽头的窗看到外面积蓄的雨水已经没过脚踝,我推开楼道铁门一眼发现屋檐下站着非常熟悉的人影,灰蒙蒙的天还在落雨,他撑着一把黑色的伞,略显单薄的衣衫。
他正好转过身来看,立刻把伞撑在我头顶,喊了声程小姐,然后指了指不远处停泊的黑车,车灯亮着,里头轮廓若隐若现。
“周总不放心,亲自来接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