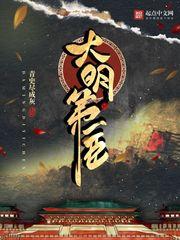笔下文学>男生真的可以爱一个女生很久很久吗?知乎 > 10 章(第1页)
10 章(第1页)
,有个人喘着大气拦住我:
「南河要发大水了,有的房子恐怕要塌了,大家都往山上跑,你怎么还下去?」
周杨从后面拉了拉我说他应该没事儿,不要再下山了,很危险。
镇诊所的大夫是个老前辈,我应该可以确定他不会很快离开。
我把车开得又快了些:「水不是还没淹过来吗,大水发过来不知道要在山上待几天,你的伤感染了更危险。」
那天的我们像犯了大罪的囚徒,任命运摆布。
天色是昏黑昏黑的,越靠近山底风却越大,整个山镇像一头巨大的猛兽要将我们吞噬,镇上的民众一波接一波向山上跑,眼前尽是兵荒马乱……
我不管不顾地冲到南坡,镇诊所大开着门,我冲进门,发现老大夫倒在了地上,我把老人家扶起来,周杨没有坐在三轮车上等我。
他走过来也帮我一起搀扶着老大夫。
我问老大夫:「紧急的药箱,还有刀伤需要的药在哪,我帮您拿上,现在先送您出去。」
我和周杨把老人送到南坡上,有人来接应,然后拿着喇叭对坡下喊:「快走了,紧急撤离了,南河要发大水了!」
我不管不顾冲到坡下,准备跑进屋拿药箱。
轰轰隆隆的一闷响——
眩晕得不清醒的意识里,还是能感觉到有一个人死命把我护在他怀里。
周杨撑在我身体前面,我们两个蹲在一个狭小的角落,房梁斜立在我们面前,挡住了其他塌落的重物,地上的水刚没过脚踝……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伸手抚过他的肩膀、手臂、后背……试图检查他有没有受伤。
「林漫,这时候耍流氓不合适吧?」
我一点都笑不出来,听着他略显艰难的喘息,又开始止不住地抽泣。
我问他:「你的伤口是不是很疼?」
「还好。」他说,「都说不让你来了,如果你出不去,你知道我会有多自责吗?」
我摇着头对他说:「对不起,周杨,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他费力地伸手抚上我的脸:「你别哭啊。」
空气冷而潮湿,地上的水已经蔓过小腿腹,浑身冰冷直至骨髓。
周杨把头搭在我肩上,我靠着墙,断断续续昏睡到一束光从缝隙里照进来……
「林漫,我爱你。」
我们四目相视——
我笑了笑,认真地告诉他:「我也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