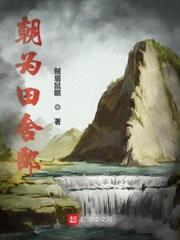笔下文学>我所行之地翻译 > 第127章(第1页)
第127章(第1页)
>
至少他能看出来,薛从之和沈骞确实是不同的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能做的事,也合该完全不同。
沈逸端起了那杯已经温凉的茶水,慢慢顺着气力喝进胃里。他被这样的暖意重新填补起来,一时间想起太多理不清楚的事情。
他闭上眼,那些于他现在都没什么关系了。他只是想再见一见他的阿姐,再多陪一陪他的阿娘。
这么说来,或许他要是能醉,就该和柳千山一样了,滚在地上或是吃力地站起来摇晃,只想喝酒,不要做官,不想身边的人死,甚至,不待在长安城中,不要这爵位,都可以。
第二十一章
沈逸撑了纸伞站在庭院当中,本该越聚越多的蝶被春日突来的雨一并驱散了。淅沥的细雨从簇成明黄的花蕊中穿过,沾湿了地上的沙砾。
自那夜分别,再赴歌楼春宴自己却不再见薛从之身影。恍若醉时一场梦,他垂下眼去看水攒在坑洼里,一滴一滴。
他不该如此焦急,沈逸开解着自己。昨日唤府中下人已经给薛珩送去今岁的新贡茶,现在想来,他从天家那里得的封赏,怕是比侯府用度还要奢华不少。
雨打在伞面上,天气渐暖,霍氏平日调养身体所用的药方也换了更温和的草药。只是仍旧闭门不出,偶尔出来也都是由侍女扶着,到亭中赏赏花。
沈逸回府时碰见过一两次,上前问安后霍氏便不爱答话了。和自己静坐片刻,霍氏就起身再回了房中。
他撑伞往院边走近了两步,免得雨将刚绽开的花瓣打落在泥里。
霍氏这两日还不曾出来过,要是连这些花都先谢了,他的阿娘怕是更不愿意出来走一走了。
“小侯爷——薛大人也回了份礼,”沈逸回头看到下人端着木匣冒着雨走近了,“现在我去放到小侯爷房中?”
“我现在拿着便是,不用那么麻烦。”沈逸从他手中抽出那个看起来便素净的木匣,因还撑着伞,便将木匣塞到了袖间。
指尖摩挲过上面粗糙的磕痕,他却没有第一时间拆开去看一眼。沈逸瞧着越来绵柔的雨,如今再吹面的春风带来的就是暖意了。
他掐下一朵开得嫣红的花,伞面斜下来一瞬让细雨沾了衣。他想,自己如今还能按捺住心性,等到薛从之开始起事。
想起沈婠来,他又将手中的那朵轻放进草间。就是要劳烦他的阿姐,再等等,再等等他,等等以后的春景。
春雨渐渐歇了,沈逸回到房中掩好了窗。方拿出来刚才塞到袖间的木匣来,上面松动的锁扣一撬便开。
明黄的绸布上铺了一小盅茶叶,不用凑近就能闻到一股清淡的茶香。不过两相来往,礼品算是次要。
沈逸掀开了触感厚重的绸布,在匣底摸出一张字条来。他展开那一小张字条,又很快点了烛火,亲眼见着那张字条被烧成灰落在桌案上。
至于指尖的烧灼感便是习惯了的,薛从之一上来,倒是先要讨他养了经年的白鸽。
罢了,沈逸还是起身去了鸽笼处。正巧沈骞不在府中,今日遇雨,白鸽难得都待在笼中挤在一起。他收起伞,在雨幕里将笼中的白鸽一只一只捉出来挑着。
生了杂羽的自然不好送信,还有些性子顽劣没有驯好的新鸽。他由着鸽子扑腾蹭了他一身的落羽,才捉进手里三四只。
打算一只交由庖厨分炖给霍氏养养身子,剩下的绑在一起送到薛府去。
纸伞被擦肩而过的风吹掀在一旁,又滚落着沾了些泥泞。沈逸顾不上那把伞,淋着春雨挨个吩咐过府中新来的小厮。
见他从府中撑伞出去才回到鸽笼处,沈逸捡起了那把纸伞,这时却是外衫尽湿了。刚经过一遭捉捕的白鸽缩在笼子更深处,只剩下豆大的眼珠不断向外看着。
他重新点过白鸽的数目,不打算今年再添新鸽。沈逸关上了鸽笼,转身走回房中。
暮色渐深,云影未散,长安城的这场春雨,倒算是停下了。
之后和薛珩再有消息往来,便也是用府中的白鸽传信。方升上位,薛从之倒还同往常一般,少有出门赴宴的时候,但若有登门之客,却是来者不拒。
开满庭院的花一次性落了干净,白鸽换了新羽显得更难看了些。沈逸计算过庙堂所用之物,自己上面那位郭奉常,为人甚至还不如沈骞之流。
又实在糊涂,账目用度一律堆了数年,翻找起来只说自己糊涂,再细问起来的时候只会点头称是。似乎还是碍着自己世子的身份,偶尔一见,让人一看也难知官职上下。
他提笔理过其中要物,剩下算不清的账倒不急用。沈逸誊抄着往年的用度,又算过今年新添之物。
天家那位倒是肯拨下更多年俸交给庙堂之中的筮人神官,因是闲职,每月立于朝堂只有两三日。他去时也更爱往远处望着自己本来看不见的偏殿,至于居在上位的那位陛下,不如暂避。
金银之物按数录入竹片之中,他望着增加不少的数目轻笑一声。原来,高坐椅上的陛下,也信鬼神,也信福祸。
好像与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却坐看万人生死挣扎,却坐看白骨成堆,旁人离散。
薛珩再送来的字条上也都是琐事,无非是以侯府的名义多收几封拜帖,还有便是写了密文交与他。
沈逸抽出竹简来,想了想还是将字条放进自己枕边的木匣之中。上面的墨痕记下圣贤的仁义,他停下掠了一眼其中注解,又卷起来一齐放在房中。
他只剩下最后半卷没有记在脑中,好在薛从之近来动作不大,没再给他递上新的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