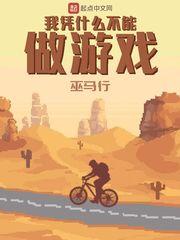笔下文学>重生甄嬛传之陵容 > 第224章 自作多情下(第1页)
第224章 自作多情下(第1页)
因此含泪一笑,又亲自为林秀拭泪:“母亲这是说什么?”
“我与哥哥,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宝哥儿也是。”
“或许我和他在这件事上的看法不同,可是一家人总是一家人,这是无法改变的。”
“若是连自己的母亲、兄长都无法信任,那么我和宝哥儿、英哥儿,就无法在宫中立足了。”
林秀见陵容说的直白坦诚,也久放下心,将安陵宇的计划和盘托出。
原来,哥哥早已安排了后手。
他曾经在陕甘一地呆过一段时间,和一个叫方知我的和尚是旧交。
这和尚荤酒不忌,自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行为放诞,乖张不俗,为寺院所不容,因此单赁了一处小院落,以教人武艺为生。
在家时,哥哥还曾来信说过此人,据说他力大无穷,武艺高强,膀大腰圆,是个十足的西北汉子,十数人来搬她,也搬不动。
哥哥与他,有半师之谊,当年曾在寺院后面的书院读书,二人常常往来。
因此宝哥儿受令去往陕甘,那和尚也就动身出发前往青田县了。
再有四妹的夫婿,是专管玉石的皇商,虽说只管一小种,可是时常往西北走动,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宝哥儿们出发不久,这伙皇商也就出发了,只是包裹中除了装有采买玉石的金银细软,还有刀枪剑戟。
再有兄长的一个同年,“正好”也在那里严查走私私盐、私茶的案子,如今正落脚在离青田县不远的孜川州。
若需策应,疾驰两个时辰便能到达。
前日,陵容托人传来回去,陵宇又安排了一队人去那里游学,带头的,就是刚刚考取童生的安陵宽。
陵容不可置信地抬起头:“娘,宽弟今年也不过十二岁啊。”
林秀忍不住拭泪:“是啊,这还是这孩子自己要去的呢。”
“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陵容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感动,为了宝哥儿,哥哥将自己明的、暗的关系都动用上了,就连才十二岁的宽弟,也要去陕甘。
“娘,萧姨娘她也肯?”
林秀笑道:“你萧姨娘是什么人?”
“咱们家是怎么起家的,她最是明白,当年还是她送你参选的呢。”
“咱们既然选了这条路,那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若是宝哥儿不好了,别说宽儿,就算是嫁出去的几个丫头,恐怕都没什么好下场。”
听着母亲的语气,似乎已经知道宝哥儿意在皇位,陵容忍不住说:“娘,你,你说什么?”
林秀慈和一笑,拉着陵容的手说:“你们都以为娘傻是不是?”
“你以为,当初安比槐的后院,争这个、争那个,最后是为了什么?”
“这后院,不管是皇家的,还是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若是女人多了,孩子多了,就只会争一样东西。”
“就算你不争,周围人也会推着你往前争。在这个位子,不争也是争。”
林秀的目光意味深长:“珚珚,你已经下不来了。”
陵容终于忍不住扑在林秀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还把熟睡的英哥儿也吵醒了,于是林秀只能先哄了女儿,又哄了小外孙,忙地不亦乐乎。
陵容红着脸道:“这段时间,我不爱搭理哥哥,娘,你回去,跟哥哥说,就说我不怪他了。”
林秀听了,促狭一笑,问道:“按理说我被封为宁国夫人,那么阳都侯夫人的爵位就空出来了,你嫂子也可上书请封,然后递牌子入宫看望你,你知道她为什么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