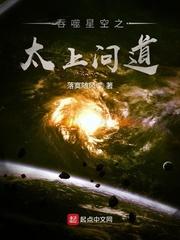笔下文学>荒原玫瑰蜀七笔趣阁 > 第154章 第三种绝色(第1页)
第154章 第三种绝色(第1页)
忙碌的十月份过后,入深秋。
十一月的天渐入佳境,秋过,冬便来了。
一叶知秋,一夜入冬,从秋入冬可以是一瞬间的事,也可以是漫长等待的契机。
如果注定要跟她白头偕老的话,我想早点把她娶回家。
这样的情话不是某位酸臭的诗人写的,而是程澄亲口说的。
从确认结婚,到双方父母制定婚礼细节,筹备婚礼,以及全部嘉宾出席婚礼,只用了三个月。
12月12日,在这个寒冷却喜庆的日子里,程澄不再孤身一人,路姮也成为了某人的妻。
在这场盛大又奢华的婚礼上,出席的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企业员工,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他们的婚礼更像是一种商业社交活动,互相递名片,邀请可以联姻的少爷小姐跳第一支舞。连君城萧那样张扬又美颜的人都只能排到下下签。
明明是血腥的竞技斗兽场,却被伪装成相亲相爱包饺子的过年戏码。
这场婚礼的主角,对此不屑一顾,反正都是做给父母看的,功利不功利有什么关系?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牵着的手是自己想牵的,礼服也是自己精挑细选满意的,无名指上的戒指也是充满期待的。
一开始,林榆并不想来,她祝福程澄,虽然见面屈指可数,但因为是邵牧原的朋友,而且他很好相处,是个不错的人。但,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她就已经被框死在一亩三分地里,她的脚步迈都迈不出去,更别说要一步跨进那么遥远又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还是那句话,与邵牧原在一起已经花光了她所有的勇气,她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剩余的气力去迎接避不可避的恶意与蔑视。
她从未讲过缘由,但邵牧原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为此感到愧疚,可他又有什么值得愧疚的呢?
所有人的出生都是注定好了的,可以有权利自哀自怨,但没有权力怨天尤人。
那天去取礼服,韩叔伯倒成了最有力的说客。
他们坐在围炉煮茶的一边,窗外北风呼啸,室内温暖如春。
韩叔伯说,“丫头呀。。。你这个人呢,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想太多啦!”他咧着嘴笑着,摸一把胡子开始掏心窝子,“人这一辈子呀,是活不明白的,就像你韩叔伯我,半截入黄土的人了,还是没想明白我这辈子到底在拼什么劲儿,可是后来我又想明白了…丫头你才我想明白什么了?”韩叔伯有些卖关子。
林榆摇摇头,有些好奇。
韩叔伯嘿嘿一笑,眼尾的褶皱更深了些,“我呀…想明白了…”他神情似是有些恍惚,恍惚间又无比清醒,“人这一辈子要做的选择太多,而每一次选择都会因为各种瞎扯淡的原因后悔,既然选不选都会后悔,那你又在怕什么呢?年纪轻轻的,可不兴前怕狼后怕虎的,”他抬手拍了拍林榆的脑袋,“就算最后真的不尽人意,那又怎样呢?生离总好过死别。”他站起身来,腿脚有些颤颤巍巍的,“死老头子内急…丫头别见怪啊!”
她回以一个微笑,瞧着那副有今天没明天的身子,没来由的心酸,‘生离总好过死别’,或许韩叔伯又想起了他的妻,他的子,对他而言,死别才是最难以释怀的心痛。
亲手将礼服交给林榆,韩叔伯摆摆手,“多出去见见世面,好的坏的,一把抓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