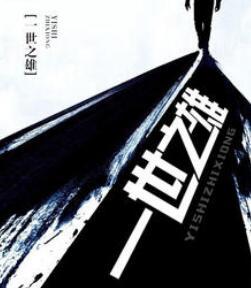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铁血残明之南洋崛起 笔趣阁起点 > 第508章 超大买卖(第1页)
第508章 超大买卖(第1页)
在几个督抚级大官的注视下,周培公将贺珍想走私川盐的事汇报了一遍。
刘兆麒细细一算,然后被贺珍的野心所震惊——走私规模实在太过巨大,大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由于船舶在江河上航行要受水流影响,所以下行装载的货物总比上行多两三成。理论上,如果船只能把九万石粮食运到东川,就能从东川运回十二万担食盐。
这可是十二万担盐呐,走私这么多盐货,贺珍的胆子也太大了!
湖广全省近千万百姓,每年也就消耗几十万担食盐而已,这一次就走私两成,比去年一整年运来的官盐还要多。
按照武汉当前行情计算,这批私盐的总价值高达两百多万两白银,名副其实的大手笔,大生意。
虽然还不知道贺珍打算以什么价格卖给盐枭,不过想来不会太高。假设贺珍以每担十两或十二两的价格卖出,盐枭们的利润空间仍非常惊人。
周培公还提到,贺珍愿意拿出两成利润来上下打点,一成给董军门,一成给经手的其他同僚。
“大胆!”
董学礼怒不可遏,指着周培公骂道:“你受朝廷大恩,竟为贼人当说客,真是大逆不道!我董某人岂会贪图贼人银两,以身犯国法?”
周培公匍匐于地,连声叫屈道:“湖广今年缺盐缺得厉害,学生的荆门老家都卖到三十两一担了。贼人说一担盐能活三四十人,学生觉得有些道理,才将此话原封转告给诸位大人。学生……学生可没有半点私心啊!”
说着,他又将两个袖口的暗袋外翻,以示自己两袖清风,没有收受任何金银财物。
刘兆麒身为湖广巡抚,掌管全省政务,对湖广缺盐的窘况非常了解。
没错,之前京城对盐政做了一些部署,比如说让山东、河东盐运司增加产盐量,同时按配额向诸省运盐。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僧多粥少就是僧多粥少,不会因为一道圣旨而改变。
几个盐运司拼了老命督促盐丁熬盐晒盐,可再怎么赶也无法弥补南方缺失的产量。而且山东盐运司的食盐走大运河一路运过来,南直隶和江西都在拼命截留,能运到湖广的份额十不存一。
吃得多来得少,价格自然一路飞涨。
刘兆麒还知道,只要禁海迁界令一日不解除,这种紧缺就一日无法缓解,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早晚有一天盐会比黄金还贵。届时,老百姓耗尽家资也买不起一斤一两。因缺盐而大面积死人的情况一定会发生,问题可能比缺粮还要严重。
刘兆麒猛然发现,贺珍所说的“天下苍生”并非一句胡话,而是即将发生,且残酷无比的事实。
想到这一点,他示意董学礼暂停呵斥,让周培公站起来回话。
“照你看来,这件事是贺珍的意思,还是伪帝的意思?”
周培公被骂得狗血淋头,一度以为自己将要性命不保,此时重新站起,前心后背已经湿透。
他重整心神,谨慎地回道:“贺贼说这是他和袁宗第两人的私人生意,并未提及伪帝。学生想来,或许伪帝也是知道的。”
“嗯,有理。”
刘兆麒想了一下,又拿出一封信件交给张勇、董学礼等人传阅。
那是吴三桂催促湖广尽快转运物资的信件之一,里面除了满篇威胁的话,还附带一份贵州紧缺的物资清单,其中第一条就是食盐。
吴三桂声称,如果两个月之内不给贵州运去十万担食盐,那么他不能保证前线军队还有力气扛住明军攻势。理由非常正当,连盐都没得吃,前线将士哪里还有力气提刀杀敌呢?
董学礼没好气道:“危言耸听。贵州缺盐缺到士卒都没盐可吃了?真是瞎扯。”
“未必啊!你们不知道,我们还能从山东、山西多少拿点接济。我们不给,贵州是一点都没有。除非……平西王去找白文选买私盐。”
刘兆麒告诉众人,贵州没有盐运司,素来不产盐——不是少,是连一丁点都不产。自从明初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以来,贵州从没在本地熬晒过一斤盐,百姓所需只能从云南、四川等产盐省份获得。
贵州既不靠海,也从来没发现过任何盐池、盐井或者其他盐矿,可以说,自古以来那里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贫盐之地,看不到一丝转变的希望。
所以,其他东西吴三桂或许不是很缺,盐却肯定非常缺,而且缺到就快把他逼疯的地步。
由此推论,如果不能满足盐方面的要求,黔军入楚抢盐的可能性非常大,几乎板上钉钉。
“那……他还可以找广西买嘛,”董学礼不服气道,“广西靠海,总会自己晒一些吧?前些天,我们不是还吃了几包广西盐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