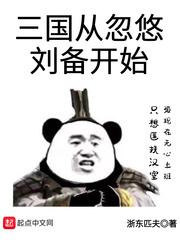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一生一世黑白影画谁是内鬼 > 36 第三十五章 此无间地狱3(第2页)
36 第三十五章 此无间地狱3(第2页)
温寒动了动身子,掌心从他的腰上滑过去,拇指扣在他的腰带上,好像这样会安心些,拉住他了。
程牧云终于笑了,轻缓的俄语从舌尖下一点点滑出:“宝贝儿,你是在想念我的身体吗?”他睁开眼,手滑下去托住她的大腿,将她托上自己的腰,“来。”
“我很怕听你说俄语。”
“怎么?难道我的俄语会让你感到不适?”他轻声笑。
她话到嘴边,又压下去:“不,很有魅力。”
让人恐惧?是的,可是现在这个时候又会是天籁。
他的眼神像咒语,让她失去抵抗能力。
程牧云,这个名字对她仍旧是个迷,可能他一辈子也不会把所经历过的那些黑暗的事,走过的那些曲折的路,见过的那些恶毒的人都告诉她。可毫无疑问,从最开始,她就躲不开他。
“你刚到中国时,中文好吗?”
“这是个很让人难堪的问题,亲爱的,你能想象出一个穿着灰布袍的僧人用俄语一遍遍念地藏本愿经的情景吗?”
温寒心神不宁地笑。
他好像是再也不会对她说中文一样,从昨夜起,就开始越来越频繁,直到现在,好像那个在火车上翻书的男人消失了。匆匆来过,出现,然后消失。
这代表着他在做什么决定,还是他只是太悲伤死去了两个好友兄弟,想起了在莫斯科的日子?
程牧云像是看穿了她的想法,直接抱着她坐起来,舌尖从她锁骨滑到耳垂:“我想起来,这次给你用的颜料有点特别,估计几个月后,你身上的HennaTattoo还很清楚,如果你不嫌麻烦,到时候找个师傅按照我的图案给你纹在身上。相信我,你在莫斯科是不可能找到比我手艺更好的人了。”
温寒答应着,想到他说的三个月后,送自己回去。
“在这里,HennaTattoo是带来吉祥如意的好东西。女人在重要的日子会特意去做,比如,订婚,结婚,”他的手掌沿着她胸口滑下去,压在她腹部,“怀胎7月,还有分娩。”
他说得每个字,一个个撞击着她的心。
“应该不会……”不会怀孕。
“是不会,”程牧云很肯定地告诉她,“相信我,我不会给你留任何麻烦。我这么爱你,怎么会让你遭受苦难?”
拥有程牧云的孩子可不是什么幸运的事情。被复仇,被清洗,被利用的命运不适合她。
温寒目光微微动荡。
她想起自己在恒河边,为一个将死的印度老人捐了烧尸体的木头钱后,对佛祖许的心愿。
原来,无论他是否爱上自己,都不会改变结局。
程牧云突然就转变话题,询问她是否腻烦了印度这种浆糊一样的饭菜,要不要吃些西餐什么的。温寒还没跟上他的节奏,他就翻身下床,像两个人的拥抱和亲吻都不存在,离开刚才还在短暂温存的木床,穿上自己黑色的登山鞋,难得一本正经套了干净衬衫和登山服外衣,摸了摸自己有些刺手的短发:“我去让人给你准备一些来,你看,这里连个仆人都没有,只能我自己去跑一趟了。”
她揉了揉自己的头发,又趴回到还有他身上温度的床上,嘟囔着:“你怎么说起来,就起来了?”
程牧云偏头,笑了笑,脚步轻松地下了楼。
然而温寒并不知道,她还在等着带回早餐的这个男人离开这幢楼后,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特警,有印度的,也有别国的,本来都端着枪准备上楼直接抓人了,看到正主自己下来倒是意外。
孟良川站在那些人当中,挺无奈,低声说,要和程牧云说几句话。那些人里有孟良川比较的好朋友,算是通融了。
孟良川走过来,想揽住程牧云的肩,手伸出去,发现他太高,清了清喉咙收回手:“这里可不比尼泊尔,有我给你压着,平白无故死一个人,调查还是要有的。尤其……你身份还这么特殊。”
不论怎么说,这种非官方的“捉鬼”行为,要真惹出人命也是命案。
万一是无辜的人命,更要有交待。
程牧云没说话,算是默认。
“你耳朵可真好,我还怕他们上去动手,吓到你女人,”孟良川说完,想了想,低声问,“你实话告诉我一句,庄衍不是你弄死的吧?要真是,别管哪国法律,你都要偿命啊,程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