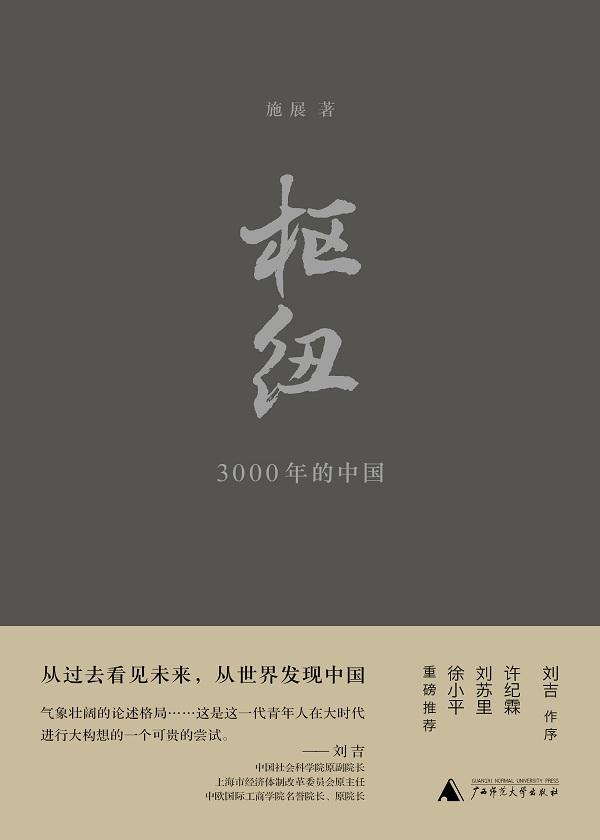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探虚陵现代篇晋江 > 470|房间(第2页)
470|房间(第2页)
师清漪一路看下来,道:“回不必问,我也晓得为何了。”
濯川:“……”
图一张一张翻过去,后头还有一张图,竟是鱼浅被人抱在怀中的模样,显是依照濯川抱着鱼浅时,低头往下俯看鱼浅的视角所绘。
画面基本被鱼浅蜷在濯川怀中的半身填满,银发披散在肩头与身前,脸更是勾勒得无比细致,依稀只能瞧见濯川揽鱼浅的手,露了一部分出来。
旁边写道:“她身有鱼尾,实在不便行动,若她不待在池中或箱中时,我便只能抱着她走来走去。今日我将她从捉妖箱中抱了出来,箱中都是水,她身湿漉漉的,水滴落在地,形成一片水渍。我踩在那水渍,一时不慎,脚底打滑,我抱着她摔在地。我怕压着她,跌倒时慌忙将自个垫在她身下,她的身子趴在我怀里,脸与我挨了一个猝不及防。她的唇碰到了我的嘴唇,我当时几乎傻了,什么都不晓得,只晓得她的唇软极了,似含着水。之后三天,我都不敢直接瞧她的脸,我怕见到她的唇,夜里想起她,便会做梦。我怕做那般的梦,却又想做那般的梦,我想我许是犯了癔症。”
鱼浅看到,不解道:“阿川,什么梦会让你当时既害怕,却又想做?你说怕夜里想起我,会做梦,梦里若是有我,你为何会怕?”
她看去有难过:“那时你怕我?可是我吓到你了么?”
濯川最怕鱼浅失落,忙道:“不是的,我那时不晓得自个怎么了,夜里竟做那般肖想你的梦,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我自个,那时我觉得我自个是个禽兽。”
师清漪:“……”
好罢,她以往也做过般的梦,梦里都是洛神。
若如濯川所言,难道她也是……
才……才不是。
濯川也太老实了,只是做个那般的梦而已,怎地如天塌了似的。
师清漪回想起她做那般梦境时的情景,面色顿时凝住。
好罢,其实她也好似觉得天塌了。
第二日醒来时,她慌忙去浴室洗去一身的热汗,出了房门瞧见洛神在客厅,她一想到自个做了那种梦,当时都不敢去看洛神。
“肖想我的梦?”鱼浅才明白,道:“你是说你做了春梦么?”
濯川面红耳赤,低声道:“你莫要般直接说出来。”
“也是私房话?”鱼浅委屈道:“那只能等你我回房说了,可惜脉井底下没有房。其实我攒了好私房话要说,但你叮嘱了不能在外说私房话,我便忍着未曾说出来的。”
濯川语塞:“鱼,我……”
师清漪听鱼浅此言,既觉得好,却又莫名有心酸。
目前外头所有房,皆不可信。
但她可以试着为鱼浅和濯川准备一个房,一个特殊的,旁人都无法窥探打扰到的房,让她们尽情说私房话,也算圆了鱼浅所愿。
师清漪宽慰她们二人道:“脉井底下没有房,但凰殿里有房,到时我们解决了脉息阻隔,出得脉井,你们可以回房说,先莫要心急。”
濯川越发局促,忙道:“师师,我……我不急的。”
鱼浅却道:“我急。”
师清漪:“……”
濯川:“……”
鱼浅忍了忍,终究还是直白道:“我难受,想说私房话,现下便想说,如何是好?但阿川让我莫要在外说私房话,我得听阿川的,但我又忍不住,何时我才能进房说私房话?”
师清漪见鱼浅神色哀哀的,无奈地叹了口气。
其实鱼浅已很是勤学好问,但毕竟是从水里来的,尚未完全适应岸的一切,她岸之有糊涂,容易被人的话带进沟里去。
师清漪道:“你误会了,不必当真有房,只要旁人听不到便好。”
鱼浅讶道:“不需要房么?我还以为一定要回到房才能说。”
师清漪指了下洛神,道:“是她教坏你了,非说什么在房中说的话。其实只是因着有情人大多欢喜在房中时说话,毕竟人私底下在房中时,不会被听到,而那般氛围又最适合说那话,才有‘私房话’般说法流传出来的。”
真是,为何她非得一本正经地在此解释羞死人的东西。
都怪洛神。
洛神面色无辜道:“我说得也未曾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