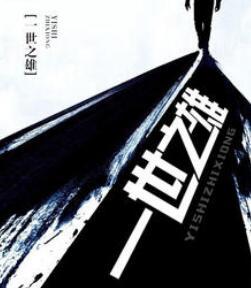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帝王之友现代提取码 > 145|142 0142 (第3页)
145|142 0142 (第3页)
崔季明僵在原地,想着干脆跑了算了,毕竟对于殷胥,她有的是一哭二抱三打炮之类的保留手段还没用上,应该还有余地。殷胥似乎看出来了,两手并在袖内,道:“你要是想跑,以后都别来见我。咱俩这辈子到此为止得了。”
卧槽……这种狠话都说出来了啊!
崔季明一个愣神,这么多年头一次兴奋难掩的耐冬,指挥着无数彪悍的侍卫,如泰山压顶般朝崔季明层层扑来,她一个踉跄,连拿刀鞘做个样子的余地都没有,就被压在众侍卫下头,被拿着粗麻绳绑的如同蚕蛹似的,扔在了马上。
她直到看着殷胥翻身上马在前,理都不理她,才半天从懵比中回过神来。
殷胥没回头,坐在马上,心中有些隐隐约约的自得。果然这样的话,也是能威胁得了她的,她也会怕他怒极了要断绝关系啊。
崔季明:“九妹你不能这么对我啊,我当年让人家突厥给抓了,都没被绑成这个熊样过啊!你……哎哟卧槽,这姿势硌得慌啊,你给我挪挪。”
然而殷胥看起来比阿史那燕罗还冷心冷面,他理都不理后头被硌到乱叫唤的崔季明,在酒铺老板娘惊恐的神情中,驮着崔季明往吴兴城内去了。
崔季明简直觉得殷胥就是被逼急了的兔子,这种时候鬼畜的令人难以想象,她一路嘴不闲的哀嚎着:“我难受,你这样我真的要吐了……啊……都没有一个人可怜可怜我,我要不是想见你,早就跑了,还给你抓我的机会么!”
殷胥装听不见。
崔季明又嚎:“你说你非把自己跟人家大姑娘比什么,我也没跟哪家娘子又亲又抱又摸过啊,我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你现在还要绑我走,还有没有王法了——下回你要是把我拖进屋里折辱,我堂堂崔家的嫡子,让你又摸又抱的糟蹋了,你的那些手下也要眼睁睁看着么?!”
殷胥让她的不要脸气的额上青筋快崩了,直接撕了她布斗笠上的碎布,揉成一团塞她嘴里了。崔季明这会儿可算是不能说话了,不过至少还能□□,她一颠簸便是一声嚎叫,只是这嚎叫被口中布团生生压成了呻|吟的音量。
他不知道别人听来是如何,反正他是听了几声便感觉后脑都麻了,不忍再听,拽着崔季明到身前来,让她侧骑在马上,他一只手捂着她的嘴,一只手拽着缰绳。
崔季明却不老实,她毛茸茸脑袋拱来拱去的。她完全没有一点被人绑走的自觉,好似想找个舒服的姿势,几次差点从马背上滑下去,殷胥不得不松开捂着她嘴的手,圈住她的腰防止她掉下去。
崔季明这回可真是满意了,她也不管自己被绑成这个熊样,活像是占了天下第一宝座般自得,将脑袋拱进他颈侧,一边蹭一边哼哧哼哧的嗅。殷胥觉得自己活像是抱了一只活色生香的肉猪,被她拱的烦不胜烦,却又只是装模作样似的躲了躲,下巴仍抵在她额头边。
直到他们一行再回到了吴兴的那家茶坊,掌柜看着崔季明如此模样被端王拎了回来,惊得扶着柜台浑身一哆嗦。殷胥伸手在她袖口摸了半天没找到,只得探到她胸口衣领内一阵摸索,崔季明瞪大了眼,拧着身子想避开他的手,殷胥皱眉:“老实点。”
崔季明被他一脸严肃的摸到生无可恋,满脸崩溃,殷胥终于找到了那块儿白玉牌子,扔在了桌上,对掌柜道:“她刚刚来找你做什么的?还是要你传了什么话?”
毕竟殷胥不是常对外露脸的,这掌柜的见他来时拿了个玉佩,那是陆行帮去年开始在南地使用的通行凭证,碧色的玉佩算不上很高级的,因此掌柜的也不知道眼前之人是顶头主子。态度自然也有些敷衍,笑道:“郎君,您抓的这位是陆行帮的座上宾,您还是先放了他,和和气气说话才好。”
殷胥斜眼:“我竟不知你成了陆行帮的座上宾?”
崔季明可是知道某人才是主上,不断朝掌柜的使眼色。或许是她眼神实在太着急,掌柜的竟理解成她在求救,更硬气道:“正是。您这位带着碧色玉佩来,便知几条道内行事的双爷,这位正是双爷的挚友,不论这位郎君如何得罪了您,还请您先放人。”
耐冬看这再闹下去,非要在这地方扯出陆行帮内的不合来,连忙拽着掌柜上前一步,掏了块玉佩给他一扫,轻声说了几句。
那掌柜回来后,额上明显多了一层冷汗,却也不卑不亢道:“也望主上了解,毕竟我也算是吴兴这边的管事,总不能在刚刚事态不明了的情况下,随便带走与陆行帮有牵连的人。”
殷胥揽着崔季明,道:“她是因何事来找您。”
掌柜面露难色,望了一眼崔季明,咬了咬牙道:“这位郎君是将信件和消息托给双爷的。”
殷胥手指搭在崔季明后脑上,好似威胁好似有意无意的点了点她发髻,道:“信呢?”
掌柜:“毕竟陆行帮讲究的就是效率,信已经送出去了。”
殷胥扯了扯嘴角:“消息呢?”
崔季明内心大叫完蛋。
掌柜脑袋都低了下去:“是口信。郎君……让双爷告知主上,她已经回了长安,之前是去了蜀地,所以才断了消息的。”
殷胥低头瞥了她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