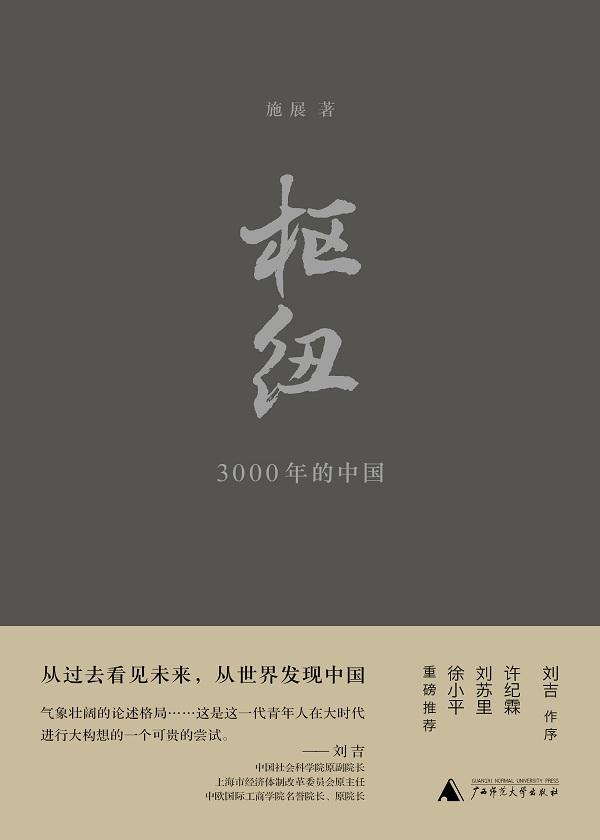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盐酸乙哌立松片的功效与作用 > 第六章 清末至辛亥革命四川自流井(第4页)
第六章 清末至辛亥革命四川自流井(第4页)
“那我怎么不记着见过你?”我好奇地问道。
“你李大少爷好金贵的。那时候你来这学堂的工地,你家管家都是先遣人来,四下看过,好生小心。哪就记得我啦。不过这事你恐怕记着,你和牧师去量那官印山,那可是我在旁边伺候着的。”
此时我终于想起了先前的一幕。与白牧师在一起的幼年时光在此危难时刻回忆起来,竟让我一时双眼酸涩,堪堪泪下。我不想在人前流泪,忙侧身坐下。
“学堂放假了,你还来看书,好用功啊。”亨利伸过手,我不再介意,便把那几本书递给他看。
“我得出去躲躲,所以借几本书,省得路上闷。”
“外面都传着你家老爷吃官司,给官府抓了?”
“家里人怕出事,要去湖北躲躲。我们明天就走。”
“那你们为啥子不来这儿躲。你看看,有好几家大户都躲进来了,哪用躲到湖北去?”
听他这么说,我想起了方才的情景,心里也确实有些疑惑,就问道:“我听家里的堂舅说,现在外面都说要灭洋人,这儿也不安全。”
“没得那么凶,”亨利不屑地说道,“你看,咱们的洋校长,今天去荣县不就是和同志军会面。还有好几家旁的教堂里的牧师和神父都一起去了,就是商议怎么不出乱子。”
“爹临走的时候也跟我说过,要是出事,就来这儿求洋牧师们庇护。我本来想着该在家里守着,等着爹回来。可那堂舅说的也都在理,孃孃和我幺妹万一碰上官兵或是革命军就大大不妙了。”
“那你堂舅怎么安排的,说给我听听。”亨利在我身旁坐下,翘起腿,静静地听我把此前几天家里商议的这些事情讲给他听。不知为什么,我们虽是素昧平生,只是有着白牧师那缘分,却觉着可以和他畅谈。
听完了前因后果,亨利脸上的神情变得难以捉摸,好似比他的年岁长了许多。
“李少爷,想听好话还是听真话?”
“当然是真话。”
“对头,听真话总是对头的。不过真话就是,你们这就是入套了。赔钱是肯定的,赔不赔上人,也是说不准。不过,我想着不差的话,钱是一准要赔的。”
亨利的话好似在我混沌的心里卷起风雷闪电。他自然也看出了我心中的反复,身子向后一仰,靠在廊柱上,跷起的腿一荡一荡地说道:“信不信由你。你说了你想听真话的。你读那么多书,总也该能看出来吧。戏文里唱的,说书里说的,那都是这么回子事,越亲越得提防。”
“那我该怎么办?”
亨利盘腿坐起,满脸兴奋的神情,似是排兵布阵的将军一般。
“要我说,就是一个字:‘跑’。你自己跑过来。你想,如果你现在闹着不走,也未必有用。说不准他们索性把你迷倒了,就强带走了。”
“那我告诉管家?”我小心地问道。
“那有啥子用?他毕竟是下人。你要是跟他说了,说不准他心一虚,不让你跑了怎么办?你现在最好就是装着没事,然后晚上就一个人跑过来,谁也别告诉。”
“可那样管家岂不是要着急死了,孃孃也未必不担心?”
亨利听了,学着大人模样,摇晃着头,满腹运筹帷幄地说道:“要是我,那是肯定一言不发,就看他们怎样,到时候你不就看出来谁是忠,谁是奸了?不过李少爷,我看你也干不来。那你就留封信,说是你自己去找爹,别的不提。”
“要晚上偷跑出来吗?”
我这么问了,实是已经答应了亨利这计策。他听出我的心意,却忍不住激我的胆量,说道:“是不是怕黑哦?哎,救人救到底,你要是怕,我就夜里在你家门外等着,接你过来,算够义气吧?”
我们约好,那晚夜过十二点,我便从家里溜出去。装着一切如常并非难事,留个字条,说自己出去寻爹,也只是举手之劳。
这些做完了,看座钟的指针一前一后向表盘顶上聚合,那才是最熬人的事情。起初我想着时间一交子夜,就跑出去。可两个指针重合那刻,心里又不知怎的扑腾地紧。深吸几口气,仍是难以平复,便想着再等几刻。
时间便是如此,任什么都停它不下。分针不急不缓地由竖转平,自己心里也像是打翻了不知多少坛罐。可就算是这样想,时间还是会向前,分针下斜,堪堪到了半点。
决心终是要下,而一旦下了,也就借着一阵紧张和兴奋从自己屋里跑了出去。此时已近月底,残月如钩,星斗也被薄云遮掩。穿几个天井,从旁门溜出去,顿时被无边的黑暗所包围。家边的路我自是熟悉,顺着院墙,摸到大门边本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此时不单单是眼前的黑暗,更是心里被抽空了。虽说只是躲去学校,可我毕竟是第一次独自离家,却如盲人在黑暗中摸索一般。
亨利如期守候在家门口那条竹径边,虽也同是在黑暗之中,可他的双眸似是能看着什么光亮,没有半点迷茫。跟着他穿过竹林,绕过池塘,尽听着竹语蛙声,恐惧也慢慢淡去。到了学校墙下,他先推、后拽地领着我爬上一棵黄桷树,顺着粗硕的枝干翻过墙头。
那晚,和亨利一起躲在图书馆边一间小屋里。自己睡意全无,而他却是听着我讲的圣经故事,没多久便睡熟了。第二天,亨利给我找了一身杂役的短衫换上,又给了我些干粮。此时学校里因为聚集了四面来避祸的,人多嘈杂,倒也是不难藏匿。我这边安排好了,亨利便又溜出去,说是到我家外面看看动静。
晚饭前他回来,告诉我天一亮,家门口就乱作一团。下人们进进出出,四下搜找。家里人该是猜不到我敢跑远,只是在老宅附近四处呼喊。过了午饭,门口来了车马,看样子孃孃、堂舅寻不见我,也就不等了,带着幺妹径自走了。
亨利劝我再等一天,待他们到沱江上了船再回去。可我担心管家此时怕是已经心急如焚,最后还是亨利想了办法,让我写了封信,他到镇上找人送给管家,只是不说明自己所在,让管家只在家里守好。
第二天天还没亮,亨利和我说他要走了。
“在这儿待着太闷了,出去耍耍,”他平常地说着。
“现在外面都在打,你不怕吗?”我担心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