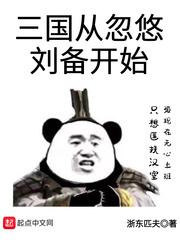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和离之后冬天的柳叶 > 80 权衡(第1页)
80 权衡(第1页)
老虞:“嫣儿,澹澹终于知道防盗了~”
陈庭宗发妻,三十岁生子伤身,开始长斋礼佛,把自己封闭在小佛堂二十几年。陈庭宗早年在朝谨慎,身边除了个徐娘半老的妾,再无她人。如今致仕,有大把的时间去焚香品茗,观画弄墨。文雅情志,只差个红袖添香之人。
男人,不管年轻与否,喜容色是天性。
找个貌美的不难,若要找个既天姿国色,又懂文墨的就不容易了。如此红颜皆是大家闺秀,谁家小姐愿给他做妾。倒是去江南拣个瘦马也好,可自小风尘里浸染,少了天然的贵气和傲骨。
所以容家和离的小姐,再合适不过了——
陈杭原不同意。要知道容嫣可是户部秦主事原配,工部和户部一向密不可分,父亲若纳了人家前妻,遇面难免尴尬。不过前几日工部上书补造漕船,本批了一百五十万两工银,被秦晏之一本奏疏硬是抹掉了五十万两。
百万两造船是够,可官场这点事,没个余银打点势必难行。许是出于记恨,许是因秦晏之青年俊才,不过二十四岁便颇受重视,陈杭心生妒忌。同意父亲纳容嫣,给这位即将上任的户部侍郎一个难堪。
所以,这事在宛平的小圈子里,很让人上心。
其实陈家和容嫣也沾些亲故,陈庭宗的同族大侄女陈氏是容嫣的亲舅母,按辈分她还得随舅舅家的表弟唤他一声叔外祖。
也真不知这位“叔外祖”如何开得这个口。
为止住话题,容嫣以修养为名,干脆闭门谢客。
想利用此事攀结陈家的几位夫人,见无孔可入心里恼急,画风转身就变了。前一刻还感喟容嫣命途坎坷,后一刻便嚼起舌根来,道她自命清高,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一个嫁过的人,没了娘家做倚仗,无依无靠,端着身段有何意义。能当饭吃吗?到头来走投无路再求人家,不更是卑微。
何况和离又不是守寡,犯得着给前夫守贞洁吗!
容嫣对此不做任何解释。比这难听的话她在通州听得多了,她只当没听到。
她以为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可还是漏了丝缝——
冬至那日,青窕请容嫣来府上过节。本不想去,可表姐是她在宛平唯一的亲人,又听闻徐井桐回京进学,她勉强应约。
最近一直忙,好些日子不曾联系,容嫣才入了伯府大门,过堂里便奔来个圆滚滚的小团子。见小姨,澜姐儿比母亲还急,抱住了她的腿。
见软糯糯的小团子支着小乳牙笑眯眯地仰头看着自己,容嫣心都萌化了,刚把她抱在怀里,小团子便环着她脖子亲了一口,这回容嫣没惊,捏了捏她的小脸。
表姐看着二人掩口笑了,倒是她身后有人道:
“快下来吧,仔细累着小姨。”
容嫣怔。
说话的是临安伯夫人。伯夫人是续弦,府里的事连临安伯都不过问,她更是躲在静心堂念佛不与人走动。容嫣在府上住了些日子,只见过她两面。今儿怎就出来了。
表姐神色无常,容嫣看了眼热忱的徐井松,隐隐猜到了些许。
自打搬出去,徐静姝也久不见容嫣,于是随嫂嫂陪容表姐在庭院叙旧,逗孩子。直到丫鬟来请她们去前院用午饭,才把澜姐儿交给乳母。三人说笑而至,还未入堂,容嫣的笑忽而凝滞,随即敛目迈了进去。
虞墨戈来了——
徐静姝虽从容,但羞色难掩,施礼时眼神抑不住地瞟着他。容嫣则平静福身,虞墨戈朝她们淡然颌首,入席,坐在彼此对面,再无交流。
徐家应是没料到虞墨戈会来,不免有点拘束,聊了两刻钟也没个主题。瞧他们这样,容嫣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了。
今儿该是为了她的事吧。
寒暄话都说尽了,人好不容易请来总不能浪费时机。况且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虞三少爷就是再无趣也不会留意无关紧要的姑娘,但说无妨。
徐井松看了一眼伯夫人,伯夫人会意含笑道:“听闻最近陈侍郎向你提亲了?”
满桌人微怔,除了容嫣。
她有心里准备。抬眼皮瞟了眼对面顿住的筷子,淡笑。
“没有。”
的确是没有。这几日她把来者的话都堵回去了,丝毫不吐口再嫁的事,人家想提也提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