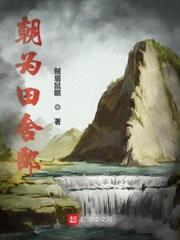笔下文学>枷锁的英文 > 101第 101 章(第2页)
101第 101 章(第2页)
“就这般他教导了逢春小半年的光景,同样的,也是对逢春抱有很大期待,望他日后能金榜题名。”林苑继续说道,希望能打消他的疑虑,“不过你也知道,逢春的身份,参加乡试考取秀才功名已是极限,哪里敢继续考下去?所以如此一来,就注定与他夫子规划的前程背道而驰。”
“逢春的事半个字都不可对外人说道,偏那不明所以的沈夫子唯恐逢春堕了志向,愈发严加盯紧逢春学业,还督促他今年春就下场考童试。恐被人察觉逢春身份有异,无奈之下,我们去岁就匆匆启程离开金陵。”
她无奈笑笑:“本以为此事就此了了,谁料那沈夫子竟不依不饶的追到蜀都来?所以你说是金陵沈夫子过来时,我着实惊讶不已。”
晋滁勾了勾唇,似有不信:“就只是木逢春的夫子?”
“不是夫子还是何人?”林苑依旧温声细语,“莫不是你觉得是我何人?若你真这般想那就未免太莫名了些,难不成凡是与逢春有些干系的,都要与我扯上边?那你怎不说他学院里那德高望重的老夫子,或许与我有些什么说不得的事?”
晋滁沉下眸,压了唇边冷笑。
那人可不是旁人,是沈文初。真是要他没法不多想。
林苑真是不解,他为何会如此多疑,为何就非认定了她跟那沈夫子有些什么。
定了定神,强压心中烦闷,她尽量平和的抬眸看他一眼:“若不信你可以让人去金陵走访查探。在金陵时的那小半年里,除了逢年过节给他夫子备礼,素日里几乎没什么交集。唯一的一次碰面,还是他因逢春进学的事,登门来确认一番。那时候在金陵,我从来深居简出,恐节外生枝,与人接触都是慎之又慎。我见了陌生人都惊惧三,纵他是逢春的夫子,我对他也是心存戒备警惕非常。你觉得我能跟他有些什么?”
本来听到他们二人见面,他横生了恼怒,暗道他们二人私下会面还不知怎样的眉来眼去,只怕就此旧情复燃了罢。可待听了她后半句,他神色蓦的一顿,掀眸定定的盯着她,眸光异样。
“陌生?”
林苑见他终于能听进去话了,暗松了口气,道:“自是。日在他自报家门说是逢春夫子之前,我就只差惊恐的夺路而逃了,着实是恐惧那些生面孔来我跟前晃的。可饶是他是逢春夫子……”她横他一眼,慢声道:“你知我性子谨慎的,唯恐暴露,与外人自是能少接触就少接触。”
晋滁盯她看了半会,试探问:“你不认得他了?”
他这话透出的信息,却是让林苑真的诧异了。
她愣了一会,问:“我……该认得吗?若是作为逢春夫子的话,我算认识?”
晋滁不错毫的盯着她眸子:“你真不知他叫什么?”
这林苑倒知道,“逢春与我提过,他夫子字为清平。”
说完后,她还兀自思索,努力在记忆搜寻与这个名字相关的信息。
晋滁见她面上不似作伪,刹那间眸光潋滟生色,唇角绷不住的上扬。
“是我记错了,你的确不认得他。”
这一瞬间,他只觉胸口那堵着的一团郁气彻底烟消云散,万舒爽。
原来,对于那沈文初她早已没了半印象。
就连清平是她父亲昔日给那沈文初起的字,她竟是半也想不起来。
纵那沈文初生的儒雅俊俏是她最为心仪的男子类型,可她半都未将其放在眼中,甚至连不记得了。也亏他患得患失,将其作为劲敌防范,白白做了这些掉的事。
“我就说,若是从前认识的,我不该没得丁点印象才是。”林苑笑笑,又无奈道:“你若还不放心的话,不妨出去问问那沈夫子,他见我时候唤我的是何称呼?对我印象又是如何?”
晋滁就挑眉:“说说看。”
林苑却含笑不语,将手从他温热的掌心挣脱开,低眸仔细整理散乱的衣襟以及梳那散开的长发。
晋滁被她的话勾起了兴趣,果真起身掀帘去了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