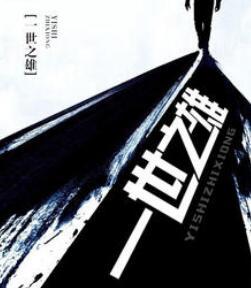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醉枕江山女主角几个 > 第一百二十章 平分秋色(第2页)
第一百二十章 平分秋色(第2页)
马桥笑笑道:“我不是这块材料,练也白搭,我想好了,上元击鞠大赛之后,跟你一块儿从军去,从明天开始,你教我武功好不好?”
杨帆凝视着他的眼睛,凝视了许久,嘴角慢慢逸出一丝笑容:“好!明早四更三刻,你到塔林等我。”
马桥挤眉弄眼地笑:“准备教我那个沾衣十八跌的功夫了么?”
杨帆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道:“等你八十岁的时候,我一定教你!”
马桥翻个白眼道:“八十岁,那还有什么搞头?”
杨帆飞起一脚,马桥“嘿”地一声,纵身闪开了。
杨帆哈哈一笑,伸手一搭马鞍,腾身跃起,稳稳地落在马背上,神采飞扬地喝了一声“驾!”便向球场中疾驰而去。
这场比赛出乎意料的打成了平局。
对禁军的击鞠高手们来说,这场比赛他们根打不起精神,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大唐第一强队,最强劲的对手是突厥队、吐蕃队,在大唐内部一向是战无不胜。而白马寺这群乌合之众,根就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
所以他们在球场上懒洋洋的,根就把这当成了应付差事的一场友谊赛。而相对的,白马寺这群人却是全力以赴,尤其是楚狂歌和杨帆。楚狂歌是当年禁军中击鞠第一高手,而杨帆连轻飘飘的藤球都能控制自如,打马球更是得心应手,这两人联起手来可谓是珠联璧合,再加上禁军的懈怠,竟尔被他们追成了平局。
到后来,禁军中这些人发现白马寺这群和尚里面果然有能与他们一较长短的高手,抖擞精神想要与他们好好较量一番时,沙漏已尽,比赛时间结束了。
超级球迷超级臭球的薛怀义哪里看得明白端倪,眼见自己这支一直是野路子,接受正式调教不足半年的击鞠队竟与大唐第一强队打成了平手,直把他喜得合不拢嘴,薛怀义喜不自禁地对丘神绩道:“怎么样,怎么样,老丘,洒家这球队很厉害吧?哈哈哈!”
丘神绩似笑非笑地道:“唔,不错,短短时日的调教,能练成这般模样,当真不错。你这位首座和尚,可肯从军么?若是他肯,某亦可在军中给他谋个职务。”
丘神绩的眼光很毒,他看得出,杨帆确实是极具击鞠天赋,这等人才留在白马寺真是糟蹋材料了,若是把他引入军中好好调教一番,必可成禁军中数一数二的击鞠高手,在一支普遍实力已经极高的队伍中,若是有个超一流高手,那种整体实力的升是不可想象的,说不定大唐可以就此改变一直以来屈居第二的尴尬局面。
薛怀义哈哈大笑道:“怎么,连我家十七你也看上了么?还真叫你猜着了,洒家想拜托你安排的那几个人里,就有他一个!”
说到这里,薛怀义挠挠光头,道:“他***,这说着说着,洒家忽然有些不舍得了。”
薛怀义挥挥手,不再去想这个问题,抻着脖子高喊道:“知客,知客!”
可怜那知客僧不能在前殿接待香客,倒成了这位方丈和尚身边的一个跑腿,一听呼喊,便匆匆跑到他的面前,说道:“方丈,有什么吩咐!”
薛怀义道:“去,好酒好肉的赶紧摆上几席,佛爷今天高兴,要与丘大将军喝个痛快!”
这白马寺佛门清净地,自打这位怀义大师做了方丈,除了色戒,早就诸戒全犯了,那知客僧已是见怪不怪,听了答应一声,就一溜烟儿地奔了出去。
薛怀义的方丈禅堂十分广大,酒宴就摆在禅房之内,丘神绩和薛怀义坐在禅床上,其他人则坐了蒲团,在青砖地面上摆开两排席案,白马寺的十个和尚坐在左侧,禁军的十位将校坐在右侧。
杨帆是白马寺首座,坐在左侧首席,距榻上的丘神绩只有一步之遥。仇人就在身畔,却还得强作镇定,杨帆的心不禁怦怦直跳。
酒席一开,黎大隐和魏勇就跑到楚狂歌身边,恭敬地先敬一杯酒,随后黎大隐干脆就坐在楚狂歌身边,与他挤做了一席。其他的将校军官对这位连丘大将军都认得的大和尚十分好奇,魏勇回到座位后,便向他们说了说楚狂歌的来历。
这些人中年长一些的虽然没有见过楚狂歌却是听过他名声的,听说这人就是当年禁军中击鞠第一高手,几个军官纷纷起身向他敬酒,楚狂歌不敢托大,忙起身一一还礼。紧接着,这些人又向杨帆敬起了酒。
杨帆的球技着实出神入化,这几位军官虽然都以击鞠自傲,也不得不承认杨帆的马术虽然并不比他们高明,捕捉战机的眼力甚至还要略逊于他们,但是只要他那根球杖挨着了马球,那等运用自如的领,实实地比他们要高明许多。
见他们敬来敬去的颇热闹,丘神绩朗声笑道:“方才薛师与某有言,俟上元鞠赛之后,就要让楚狂歌重返禁军,你们甚欣赏的这位小兄弟也要还俗入我军中,来日你们就是袍泽弟兄,说不得击鞠场上还要成伙伴,大家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不妨互通名姓,认识一下。”
那十名击鞠高手听了丘神绩的话,登时热闹起来,纷纷举杯自报姓名,杨帆这一听倒真是大吃一惊,原来这十人中倒有一大半是门庭显赫的官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