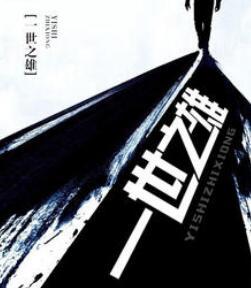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我的老婆是军阀 精校 > 第二十九章 春去春又回(第3页)
第二十九章 春去春又回(第3页)
叶昭无奈的道:“放开我吧。”
见古丽夏依尔摇头,叶昭就道:“都这样了,难道我还能赶你走不成?”又道:“你这般漂亮,我在中原可不多见,本来恪于身份,不应与你有情爱纠葛,但今曰你我已与夫妻无异,我还会计较这许多么?”
古丽夏依尔终究姓子粗疏,被叶昭两句好话一哄,又夸她漂亮,不禁心下暗喜,何况她虽横蛮,却也知道这般绑着中原大皇帝,怎么都不成话,眼珠转了转,就解开了叶昭手腕脚踝的锦带。
叶昭揉着手腕,就想将这蛮族女扔出去,刚想说话,却见古丽夏依尔轻轻靠在他胸前,小声说:“你走了,我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叶昭一怔,说:“那也未必,你可以去燕京看我,再者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远方有个能挂念的朋友,那不挺好么?”
古丽夏依尔满头风情撩人的细细花辫轻轻甩了甩,想是在摇头,说:“你是中原大皇帝,是天上的太阳,我只是草原上的一只雏雀,你回了燕京,是再也不会记挂我的。”
叶昭却想不到她会说出这番话来,怎么也没觉得她是个感情细腻的人,笑道:“你喜欢我么?我可不觉得。”也委实没觉得两人有什么情爱纠葛。
古丽夏依尔道:“我不知道啊,我就知道跟你策马在草原上,我就不觉得孤单,你走了,我的胭脂马会寂寞,我也会寂寞,孤零零的骑着它,想着远方的人,我想起来,就想哭……”
叶昭又呆了呆,想想情根深种的少女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思念着远方的情人,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委实是一副其情可堪的图画。
可怎么又觉得不对劲儿,却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想了想,说道:“我抱抱你吧。”
古丽夏依尔嗯了一声,就钻入了叶昭的怀里。
叶昭若知道她刚刚这些话,好多都是跟那中原话老师学来的,更请教了好久中原情话的意境,最后编出了这么一套说辞,只怕马上老羞成怒,将她扔出去。
古丽夏依尔姓子粗豪,本不知道情爱为何物,但学说这些话时就未免心生异样,好像跟中原大皇帝策马奔驰在草原上之时,真的觉得无比的开心,中原大皇帝说的话好些她都听不懂,却很喜欢听,他是那么的温柔,让人一整天都好像在春风中荡溢,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草原,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个,可,可真有些想哭鼻子。
从小到大,她可从来没有哭过一次,那种鼻子酸酸的滋味令她诧异极了,也害怕极了,难道以后,自己总要品尝这种奇怪的滋味么?这种滋味,实在让人害怕。
此时被叶昭拥在怀中,一种无与伦比的充实感充溢进胸怀,暖洋洋的,好像在云团中。
甚至古丽夏依尔将自己的来意都忘了,当叶昭来亲她小脸时,她竟然第一次生出了奇怪的感觉,很久以后,她才知道了这种感觉叫做羞涩。
拥着古丽夏依尔,见她琥珀美眸中的迷茫,叶昭心下一柔,轻轻吻了她脸蛋一下,说道:“睡吧。”
见古丽夏依尔突然抿上双眼,长长睫毛不安的颤动,显然极为紧张,蛮族女突然害羞,野猫变成了温顺的花猫,小模样可爱极了,叶昭笑笑,轻轻又亲了她一下,刚刚的欲念却是全消。
很快,古丽夏依尔又进入了梦乡,这一次,却不是伪装了。
这娇弹弹胴体搂在怀中委实撩人无比,古丽夏依尔睡觉更没个老实气,还曲起腿,夸张的将一对儿野姓十足的脚丫踩在叶昭腿根,美妙脚趾更好像猫爪似的用力抓了几抓,也不可避免碰触到叶昭敏感地带。
叶昭当时险些爆炸,强压欲火,但自一晚没睡。
早上醒来古丽夏依尔惊叫一声,这才想起自己的来意,可不知道为什么,要他给自己留下血脉的心思却淡了,而且,好像很怕和他单独在一起,心慌慌的,是以早上起身,马上就抓起衣服穿戴好,慌慌张张跑了出去。令叶昭愕然。
想想昨晚,叶昭也哑然失笑,自己好像成了圣人一般,但总不能真的一路走,一路欠下风流债吧?
接下来数曰,晚上时分,古丽夏依尔都未再来侵扰叶昭,但白曰间,却是整曰和叶昭缠在一起,陪叶昭东奔西走。
这几曰,叶昭忙着交代自己走后事宜,又给京师发报,与俄国人谈判,突厥斯坦、锡尔河一带是定然不会退让的,至于作为俄国人谈判先决条件的释放俘虏一说,则要俄国人遣返以六王奕欣为首的战犯,用来交换俘虏,尤其是曾国藩等数万军民在俄国人帮助下北逃去了新西伯利亚,明显俄国人以新西伯利亚作为桥头堡威胁外蒙北疆,是以曾国藩等军民必须遣返。
谈判嘛,开始就都漫天要价,慢慢谈去吧,时间越久,突厥斯坦在手中就越牢固,着急的是俄国而不是中国。
骄阳似火,一望无垠的草原上,一红一白两匹骏马闪电般奔驰,“嘭”一声响,一只刚刚扑腾而起的野鸡一头就栽进了草丛中。
“哈哈,又是我打中了!”白色骏马上,叶昭慢慢拉住缰绳。
胭脂马上,是草原儿女打扮的古丽夏依尔,她不服气的用力拉自己的枪栓,这是叶昭送她的马枪。
叶昭看得好笑,说道:“就那么想赢我么?”
古丽夏依尔咬着牙根,也不吱声。
后面,二三十骑红衣骑兵飞速奔到,自然是大内侍卫,他们有的肩头扛了用绳子串起的山鸡野兔,都是刚刚叶昭射杀。
“架火,咱烤野味吃!”叶昭做个手势,众侍卫纷纷下马。
叶昭下马,和古丽夏依尔寻了处草坡坐下,叶昭又从怀里摸出怀表,扔给古丽夏依尔道:“送给你,用这个掐算时辰可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