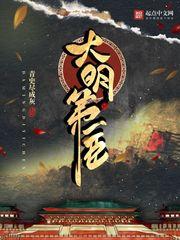笔下文学>枢纽3000年的中国pdf > 第三节 普遍帝国及其瓦解(第2页)
第三节 普遍帝国及其瓦解(第2页)
2。回纥之变
757年,眼见哥舒翰的失利,唐朝被迫转向已在蒙古高原上取代了突厥汗国的回纥汗国借兵,回纥军队在牟羽可汗的指挥下收复了东都洛阳。此时由粟特人带来的摩尼教正遭受大唐的打压,几个摩尼高僧便主动追随牟羽可汗去到漠北,没有多久,摩尼教就成为整个回纥帝国的国教。这对粟特人与回纥人来说是各取所需,回纥人通过具有宏大宇宙论的摩尼教而确立起相对于中原的精神主体性,粟特人则通过对回纥人的皈化,而使后者变成自己坚定的支持者。再后来的草原霸主,虽然不再信奉摩尼教,却在佛教(明代中晚期以后又落实为藏传佛教)当中找到了主体性的根基,也是类似的一种历史逻辑。而正是由于以西域作为通道传来的这些宗教不似儒学一样有地理依赖性,才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结果。
两种(甚至更多的)精神主体性,在统一帝国内部共存,这样一种现象从大辽开始、在元清两代获得完整呈现,其必须有超越于诸种精神要素之上的信念,以为帝国的统一精神要素;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一种寻找新的正统性叙事,构建统一的、具有超越性面向的历史记忆,以作为凝聚帝国之精神要素的运动。元明清三个朝代对于宋辽金史如何编纂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对这样一个正统性叙事的寻找过程。这样一种历史编纂问题,本质上来说就是帝国的自我定位问题——帝国究竟是中原本位或北族本位的,抑或它应该是超越于诸构成要素之上的普遍帝国?伴随着答案向后者的逐渐偏移,“大一统”的意涵、儒家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于是才有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庞大中国。帝国的自我定位这样一种问题在以前的朝代中也曾经存在过,但以如此尖锐深刻的方式获得呈现,其最初的动因实可追溯至安史之乱后的各种变乱,尤其是这段历史对草原方面的精神自主性的深刻影响。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又遭藩镇割据,国道中落,几欲覆亡,回纥回鹘汗国成了大唐的保护者,在藩镇对大唐构成威胁的时候还会出兵助阵,目的是维持一个可供不断榨取保护费的对象。粟特人遂帮助回鹘汗国出谋划策,如何从大唐更有效率地榨取保护费;回鹘汗国投桃报李,要求大唐在多个重要城市修建摩尼教寺院“大云光明寺”,帮助摩尼教再逆袭回大唐。回鹘汗国又从粟特人那里借来了字母,发明了回鹘文字以取代不敷使用的古突厥字母(直到今天,蒙文、满文应用的还是这种源自粟特文的字母),回鹘汗国走上了一条迅速文明化的道路。它从大唐榨取了大量的财富,需要找到地方存放,于是回鹘成为蒙古高原上历代游牧帝国当中,唯一建筑城郭的汗国。文明的进展,意味着武勇的消退;城郭的建设,则是游牧帝国的一个大忌,因为这样一来,游牧帝国赖以形成令人生畏的战斗力的高度机动性,将被无法移动的城郭所绑定,游牧者兵民一体、生产、生活、战争密切结合的组织特征也将分化掉,游牧帝国人口不足的劣势便立时呈现出来,遇到危险时难以自保。这些都使得回鹘汗国在840年遭遇黠戛斯人的攻击时几无还手之力,迅即亡国。
亡国的回鹘人分为几支四散逃亡,向南逃入中原地区的逐渐被同化掉了;向东逃入契丹地区的,后来有一支述律氏改为萧姓,世为大辽国的后族,深度影响着大辽国政,塑造着中国历史;但是对于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当为向西逃亡的回鹘人。西迁回鹘又分成了三支,一支西奔进入七河流域,征服了游牧于当地的葛逻禄部落,建立了喀喇汗王朝;一支投奔“安西”,在今天的哈密、吐鲁番一带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后又称西州回鹘);还有一支投奔当时尚未亡国的吐蕃,在甘肃、青海一带建立了甘州回鹘王国。
3。西域新命
回鹘西迁对后世的首要影响是,它改变了中亚的人口结构,使得中亚原本由粟特人所主导的定居区域也开始突厥化了,中亚的历史就此也进入了一种新的节奏。高昌回鹘转作定居,居于大中亚的最东端,它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8、9世纪曾是摩尼教的世界中心,于此之外,则影响力不大。毕竟游牧民族一旦定居下来,其人口基数太小的劣势就完全显露出来,只能作为一个受制于人的小团体存在了。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的那一支回鹘力量有着更大的历史意义。它的统治中心就在七河流域这片中亚的王者之地,逐渐征服了除高昌回鹘之外的差不多整个大中亚范围。它在999年击败了当时统治中亚的东伊朗系的萨曼王朝,巴托尔德曾就此评论道:“当时谁也未必理解到这一永远终结了土著的雅利安人统治的历史事件的意义。”
与匈奴、突厥或是中原王朝对于中亚的间接统治不同的是,喀喇汗王朝对中亚进行了直接统治,它本身就是个中亚王国。这个王朝的北部仍然游牧,有足够强的力量,足以自保以防漠北蒙古高原对中亚的征服;而早年在粟特人的帮助下,回鹘人在漠北的时代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懂得对中亚的定居文明该如何治理,从而有能力统治河中和天山南路的定居地区。于是以喀喇汗王朝为载体,中亚进入一种较为完整的自治状态,不为外界所制。这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以往中亚总是处在某个外部的游牧帝国或轴心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喀喇汗王朝的建立,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这样一支高度组织化的突厥力量,近乎以帝国中心整体转移的方式入主中亚,并且它的势力范围仅及中亚;此前的突厥游牧帝国对中亚的控制,则从来不是一种组织性的帝国中心的转移。正是这样一种原因,使得回鹘的西迁,有能力令中亚的定居地区也开始突厥化;其他时候的游牧帝国迁徙,则从来不会对中亚的定居地区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当然,所谓中亚的突厥化,也是个中亚的土著雅利安种粟特人与北亚来的蒙古人种回鹘突厥人互相渗透的过程,他们的生活习惯相互影响逐渐趋同,种族间的混血逐渐使得相貌也趋同。
还有一点是信仰的趋同。在回鹘西迁之前,经过阿拉伯帝国以及萨曼王朝等的多年统治,中亚地区已经伊斯兰化了,但是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突厥人,此时虽在中亚来来往往,却仍未信奉伊斯兰教。喀喇汗王朝则开始了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进程。喀喇汗王朝的先祖原本是被粟特人皈化为摩尼教徒,到了粟特人的老家又一次被其皈化为穆斯林。就回鹘突厥人来说,在漠北的第一次皈化可能首先是出于对外“索取”文明的需求;在中亚的第二次皈化,则应该首先是出于统治的需求,以便获得治下臣民的正当性认可。虽则回鹘在漠北的时候已经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但毕竟时间太短,作为一个总体秩序而言,也不那么系统,到了中亚,看到当地伊朗语系人群所传承的高度发达的治理秩序与文明成果,心向往之,则是很自然的事;伊斯兰教本身呈现着较强的秩序性特征,相对容易被回鹘突厥人一并接受下来。在喀喇汗王朝之后、清朝和俄罗斯之前,入主中亚的主要王朝,一个是统治不足百年的西辽,一个是蒙古帝国留下的察合台汗国,以及从察合台汗国衍生出的诸多后续汗国,除了西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应该也是类似的逻辑。
四、吐蕃的聚与散
雪域高原在松赞干布治下发展为雄健有力的吐蕃,松赞干布又持续不断地通过对外战争获取财富,以形成赞普的朝廷对于有离心倾向的贵族们的力量优势,提升整合能力。这也构成松赞干布的后续者们持续的战略基础,无论是权臣当政,如松赞干布重臣禄东赞,他本人及其噶尔家族在松赞干布身后主政吐蕃近半个世纪,还是其他的赞普当政,他们的利益都在于吐蕃中央朝廷的政治集权,以压制贵族,故而都坚持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但是吐蕃的这种生存逻辑与大唐的帝国战略之间构成了直接冲突关系,两者因此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对于吐蕃来说,青海与西域(及河西走廊)都是其必争之地,青海更多的是作为对外通道存在,西域(及河西走廊)则是它必需的财政来源;吐蕃与大唐争夺的主战场在青海一带,其在西域大规模用兵的能力势必受到削弱,因此在这个方向上便不得不与西突厥乃至后来的突骑施联手。对大唐来说,这样一种南北联盟会让自己在西域遇到麻烦,因此便在更西的方向寻找到盟友大食(阿拉伯帝国),形成东西联盟。如此一来,汉代的匈奴、西羌的草原、高原之南北关系与中原、西域之东西关系的对峙结构,在大唐时以突厥、吐蕃之南北关系与大唐、大食之东西关系的形式,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展开,内亚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地缘战略大十字。当然,吐蕃有时也会与大食联手,以达成别的战略目的。而大食帝国带来了一种新的精神秩序——伊斯兰教,使得内亚地区的博弈关系由此进入到一种更加复杂而又微妙的情况。
大唐与大食的联手,一度让吐蕃陷入很大困境。人们经常谈及大唐与大食在751年发生了怛罗斯之战,实际上此战役并没有那么重要。大食早在很久之前就已进入中亚,长期与大唐有着微妙的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怛罗斯之战后,大食与大唐在中亚的关系,以及中亚诸邦的状况,都没有实质性变化。真正实质性的变化来自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大唐不得不从西域-中亚调军东守,吐蕃获得了天赐良机,迅速攻占大片西域疆土,并随即与刚刚崛起不久的回鹘政权开始了在西域的反复争夺。
吐蕃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博弈关系,影响着吐蕃内部赞普与贵族群体之间的力量均衡变迁,在精神秩序的层面上反映为普世佛教与多神苯教之间的命运变迁。开始于松赞干布的佛教“前弘期”,在其身后曾几经波折。在赞普能够引入外部资源使均衡偏向自己时,佛教会处在相对优势地位,比如赤德祖赞与大唐形成和议,大唐派出金城公主和亲,佛教一时力量大盛;而赤德祖赞去世,其子赤松德赞幼年继位,朝政被贵族把持,遂开始了一场“灭佛运动”;到赤松德赞成年之后,吐蕃在西域力量大盛,力量均衡又转回到赞普一边,他压制了贵族,并推动了又一次大兴佛教的运动。
792年,赤松德赞还主持了一场“顿悟派”的汉传佛教与“渐悟派”的印度佛教的大辩论,并裁定印度佛教胜利。这一场胜利意味深远,它预示着数百年后高原与草原在精神层面上形成新联合的可能性。在札奇斯钦先生看来,经过汉文化融合的中原佛教,远不如密宗色彩浓重的印度佛教更合于吐蕃的文化;印度佛教的密宗气质既可以压制原始的萨满信仰苯教,又能把它融合起来,适合吐蕃游牧民族信仰。后来的蒙古游牧者选择了藏传佛教而非汉传佛教,原因也在这里。
赤松德赞之子赤德松赞在位期间,累年对外征服获得大量财富,帝国内部的力量均衡继续朝向赞普一边偏移。赤德松赞遂对官制进行改革,在政府中原有的众相之上设置僧相一级,力图用与赞普结盟的僧侣官员来实现集权,压制苯教贵族所掌控的众相。下一任赞普赤祖德赞,规定每七户庶民供养一位僧人,并将僧寺附近的土地民庶划作寺产,不向政府纳税,贵族众相所主导的政府进一步被赞普从财政上架空。高度崇佛的背后,隐含着赞普不断集权的努力;吐蕃的政治成熟度倘能继续向前发展的话,从逻辑上说,佛教在未来会被赞普做建制化改造,僧侣官员则会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化为赞普的官僚系统。
但这种逻辑并未获得机会展开,因为一方面,对于贵族的压制会带来贵族的强烈反弹,赤祖德赞因此而被刺杀,上台的新赞普朗达玛在苯教贵族支持下开始大规模灭佛;另一方面,也是更根本的,集权政治所需的政治成熟度远大于分权的贵族制,其财政需求也远高于贵族制,反过来也就意味着,集权政治的脆弱度在其初期同样也远大于贵族制;除非有稳定且较大规模的财政支撑,否则集权政治的努力不可能成功。由于雪域严酷的地理特性,治理成本过于高昂,吐蕃的政治成熟度无法内生地发展到能够真正支撑起集权政治的程度,赞普的财政是非常脆弱的。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的努力,已是吐蕃内生的政治秩序所能达到的极限,这是各种历史机缘的耦合才能达到的高度,一旦这些耦合被打破,则其内生政治秩序也就走到历史终点了。
吐蕃亡于内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亡于其财政脆弱性。840年,逃奔吐蕃的回鹘人,于甘肃、青海一带建立了一个附庸性的甘州回鹘王国。甘州回鹘所处的地理位置,刚好横亘在吐蕃核心区与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它在其中略微截流一下,则高度依赖外部财政的赞普马上就会遭遇到困境。因此,840年之前赤祖德赞遇刺,朗达玛还能够继承一个统一的吐蕃;而朗达玛在842年遇刺后,吐蕃内部马上陷入大规模混战状态,再无人有能力获得足够的资源以将帝国统一起来。雪域高原在中世纪那令人目眩的帝国事业从此灰飞烟灭,急速回到低成熟度的政治状态。
强大的吐蕃如同流星划过夜空,消失在历史当中,这也为“后弘期”教权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五、技术进步与豪族社会的终结
1。人口变迁与新的技术应用
安史之乱后,天下藩镇割据,帝国已近名存实亡。玄宗意图压制的豪族,居然通过安史之乱而衰败下去,这从反面说明了,唐朝皇室与豪族实际上是共生关系。大唐依靠豪族而建立了世界帝国,但其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帝国治下的和平,促使人口滋长繁茂,而可供分配的土地是有限的,曾构成帝国组织基础并带来帝国生命力的均田制势难持续,土地逐渐转为私有制,可以自由买卖,府兵制的基础被侵蚀掉了;皇帝的野心,使其欲图离弃豪族,却并没有相应的替代制度来完成帝国治理,于是皇帝会伴随豪族共同为帝国殉葬,此后仍然在位的皇帝只是在等待那缓期执行的到来。
最先开始割据的河朔三镇,所占据的华北地区正是此前帝国的财政来源中心,大唐帝国陷入财政困境。但是安史之乱意外地促成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帝国在这里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并进而促成了中原的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
战乱起后,大量人口逃至江南。这次南迁与西晋末年的南迁有很大区别。东汉末年开始天下大乱,到西晋末年已持续了近两百年,中原早已形成坞堡经济;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中间也还是有一定的时间过渡,这两个因素使得豪族有时间组织起其部曲、附庸等一同南迁,所以豪族的社会结构并未遭到太大破坏,甚至东晋的豪族门阀较之在江北时还要有影响力。而安史之乱之前,正是中原的均田制、豪族经济已近解体之际,并且安史之乱非常突然,南迁者来不及有组织地行动,只能零散地南奔;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淮河以南水网纵横不利于骑兵南下,所以逃难者迁至江南也就安全了,之后在江南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属于平民社会。
从上古以来直到安史之乱,除极个别时期,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以南的人口始终少于以北。安史之乱前不久,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河东、河北诸道的人口密度大致是淮南和江南两道人口密度的两倍还要多;但是安史之乱后,北方诸道人口损失极大,江南道人口也有减少,但其密度反是河南河北两道的近两倍,淮南道人口甚至还有相当比例的增加,密度达到河南河北道的四倍还要多;到了五代时候,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更是好过北方,中国的人口重心从此不可逆地转移到了南方。
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从而改变了相应区域的生产要素价格。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诸如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等,都不具经济可行性,反倒是粗放的技术、土地轮耕制更为经济;地狭人稠的情况下,则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会变得更为经济。在北魏时期黄河流域即已经存在水稻秧播技术,但是江淮地区一直到唐代前期仍然保持火耕水耨的技术和轮耕制,土地利用率只有50%甚至更低,因为此时土地要素价格远低于劳动力价格。直到安史之乱后,大规模人口南迁,江南开始地狭人稠,使得秧播技术及土地连作制在江南获得使用,土地利用率从50%提高到100%。到了宋代,在将冬小麦的种植扩展到江南的同时,发展了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从而将土地利用率从100%提高到200%。江南的稻麦复种制出现在北宋后期,成熟于南宋时期。正是由于秧播技术缩短了水稻的占地时间,稻麦轮作成为可能。稻麦二熟制不仅使江南的土地利用率提高,并且土地水旱交替使用,使土壤得到进一步熟化和培肥。而人口密度的增高,使得在江南地区修建复杂的水利工程也成为可能,再加上诸如占城稻、双季稻等新稻种的引入,这些都更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这样一种发展使得江南一下子成为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成为全新的经济要素,从而为帝国提供了必需的财政基础。韩愈曾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此语或略有夸张,但江南已成为帝国的核心经济区是无疑义的。
由此可知,所谓技术进步,不仅仅是指该技术是否已经出现,还包括该技术在给定的要素价格下是否具有经济性的问题。就江南农业技术的进步而言,其中的关键实际上是人地关系导致的要素价格变动,只有在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下降的时候,既有的技术才能在这里规模化应用,并衍生出一系列此前不存在的应用方式。江南地区浮现的新经济要素,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财政基础,使得皇帝可以此努力去对付国内其他反抗力量。
2。新的财政资源
劫后余生的大唐帝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虽然不够成功但令人钦佩的努力,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努力解决“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的问题,也解决帝国内部大军团所带来的危机。这一系列努力中,开拓性的一步首先便是财政改革。780年,在杨炎主导下,废除了因均田制崩溃而早已运转不灵的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规定将一切赋役皆折为货币,纳入户、地两税,每年夏秋分两次征收。两税法的税基从人变成了土地,原则上规定必须缴纳铜钱。这意味着帝国财政自东汉末年以来,历经数百年,又从实物财政转成了货币财政,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相对于实物财政而言,货币财政使得皇权的意志转化为政治行为的效率大幅提高,这为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方向偏移提供了可能性。而安史之乱后的江南社会结构是个平民社会,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当中有可能发展起更加发达的货币经济,使得货币财政的效率更加提高;另一方面,皇权终于获得了与平民结盟的机会,来进一步打击豪族,这使得豪族社会结构的瓦解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此后就进入平民社会了,帝国的统治直接面向百姓,而不再依靠豪族提供秩序。因此可以说,从隋炀帝开始的皇权对抗豪族的努力,到了这时终于因技术变迁而获得了政治可能性。
杨炎的改革无法拯救苟延残喘的大唐,却开启了“唐宋变革”的大门,但其更早的动力来源,还可以追溯到武后、玄宗那里。那个时代的帝国政治空间结构仍是东西关系,军事贵族、豪族的“类封建自由”之自生秩序与君权的集权秩序之间的对抗关系,是此一空间关系的基本由来。但是到皇帝与平民结盟打垮豪族,民间力量获得发展之后,则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的对抗关系转而呈现为民间的自由与皇权的专制之间的博弈关系。最终,唐朝崩溃之后,五代与大宋都定都河南,这是民间力量崛起的一个根本标志,关中本位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后的帝国首都永久性地定在关东了。对朝廷来说,其最大的威胁不再是内部的豪族力量,而是北方的草原帝国了。所以,此后帝国的政治空间结构便从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方的经济、财政重心与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之间的关系。从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便是这一转换的关键阶段。
3。平民社会与海洋世界的浮现
但是光有新经济要素的出现还不够,倘无新的治理能力跟上的话,它仅仅会打破过往的均衡,却并不会带来新的秩序,还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动荡与混乱,这是中唐以后的努力一直不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一大矛盾在于,社会结构已经朝向平民化转型,官僚体系当中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老贵族家世者在占据重要位置。这不是因为他们更为合适,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平民担纲起新的秩序治理之重任,唐代后期的“牛李党争”便是此一矛盾的呈现之一。
这个矛盾的化解,需要有另一种技术进步,使得知识传播成本大幅下降,足够多的平民读得起书,才有可能有足够多的平民可供选择进入官僚体系。这个技术进步实际上也不是全新的技术发明,而是对既有技术的新的应用。在五代时,冯道主持了国子监对《九经》的印刷工程,前后坚持了二十二年未曾中断,这是中国历史上首度大规模以官方财力印刷经典,这一工作开启了印刷术大规模使用的先河。
此前的印刷术,主要是用来印佛经的,在豪族社会,寺院是印刷品最有支付能力的主顾。五代十国时期逐渐浮现的平民化社会结构,以及此一期间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却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民间社会商品经济在很多地方的发展都好过以往,更多的平民开始对印刷品有了支付能力。这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市场,使得印制儒经逐渐变得有利可图。冯道所开启的印刷经典的工作,在此之后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商业活动,知识传播成本大幅下降,这才有了宋代科举的大发展。平民社会的官僚体系,终于可以从平民当中拔擢人才来充实。至此,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基本完成,中国的历史发展从第二轮大循环进入到第三轮大循环的周期。
平民社会的到来,还在悄然中开启了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海洋世界的浮现。始于8世纪中叶的广州的全面繁荣,预示着取代陆路骆驼商队贸易的海上贸易,东西方贸易开始了从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换。尽管这一势头被黄巢之乱严重打乱过,也被海禁中断过,但它已然预示着平民社会下,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如果用位于中国两极的长安和广州的关系来比喻的话,这一变化意味着,连接陆上丝绸之路的内陆城市长安的衰落,以及面向南海开放的东南部的兴盛;也意味着历史的天平开始急剧地由大陆的西北部向东方以及东南部倾斜。”
但唐朝末年的庞勋之乱,则仍在提示人们,中国是个草原、中原、海洋的多元复合体,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多元的作用方式,但不会改变多元本身。庞勋及其追随者系徐州人,因南诏攻陷了交州,为防备再战,这些徐州戍卒被派戍守桂林。朝廷两次不守三年之期的承诺,不许他们按期返乡,戍卒愤而起事,从桂林一路杀回徐州。巅峰时期庞勋麾下有二十万众,其控制区域刚好扼住江南通往长安的咽喉,朝廷立刻陷入财政困境。最终,大唐不得不依靠驻扎于晋北代地之中原、草原过渡地带的沙陀军击败庞勋。但不到十年之后黄巢又起,沙陀再次成为击溃义军的主力。宋祁在编撰《新唐书》时,曾总结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抛开王朝兴衰的感叹,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会注意到,桂林(交州)—徐州—代地,刚好是海洋、中原、草原的地理结构。庞勋之乱预示着嗣后中国历史在这多重结构当中的复杂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