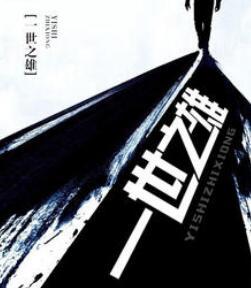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婚途似锦难重逢秦沐语上官皓 > 第250章 心思卑劣的男人(第2页)
第250章 心思卑劣的男人(第2页)
厉斯臣将她抛在大床上,覆身压上,胸口剧烈地喘息起伏着,额前垂下几缕危险的发丝,沉沉地吐气:“你们家没有教你说话要淑女,不要能粗口吗?”
他扯开自己的领口,双眼微微赤红。对着她,他做不了绅士,只想做一个卑劣的秦兽。
重欢被他这副蛮不讲理,一言不合就强上的恶劣性子气的浑身发颤,老混蛋、人渣,她能想到的所有的词都不能形容这个男人的恶劣程度。
“你要是碰我,我就告你强女干”她气的口不择言。
厉斯臣动作一听,薄唇勾起迷人的冷笑,用牙齿咬开她衣服的领口,低沉地笑道:“蠢货,我们还是夫妻,再说了你要是去告我,我就把我们上床的细节全在法庭上说出来,让法官来评判是强女干呢还是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呢。”
无耻。重欢气的话都说不出来,男人已经将她清瘦的身子完全笼罩,迫人的气息侵袭着她,低沉迷人地开腔:“你就像清教徒一样古板保守,而我一向喜欢挑战。”
厉斯臣犹如疯魔了一般,开始温柔而细致地诱骗她。
重欢第二天早上起来嗓子也哑了,眼睛也红了,险些把牙都咬碎了,那男人的技巧不是一般的好,没有半点强迫最后磨得她痛哭流涕,只求他不要再折磨她。
心思深沉到可怕,自控力强到可怕,手段卑劣到可怕的男人。
重欢瑟瑟发抖,他妈的怎么就招惹上了这个变态。
至于昨天的那点争执滚了一夜床单之后,厉斯臣闭口不提,重欢也找不到发泄口。
重欢见他沉默寡言、阴沉冷笑,一副你敢给老子惹事,敢说老子不想听的话,老子做的你下不了床的混账样子,哪里还敢质问他是不是跟重安在一起。
重欢每天见到他几乎是避着走,丝毫不敢去招惹他。
厉斯臣心情好的时候也会照顾她的情绪,让她清净地睡个好觉,不过大部分心情不好居多。
一连过了数日。老爷子依然没有醒过来,医院那边三缄其口,只是说老老爷年纪大了,还要继续观望,其实结果无非是醒过来或者一直昏迷直至死亡。
重欢见到这种情况心里也是凉了半截,每天背着人总要偷偷地擦眼泪,人前却不露一丝的脆弱。
重家到了她这一代,父亲妹妹都相继入狱,爷爷病重,重安恨她,她每日纵然住在这顶级豪宅,却有种悲凉之感。
重安重笑她可以不去在乎,可是父亲要是出来的时候,爷爷已经不在,她要怎么跟父亲交代?
许是见她郁郁寡欢,厉斯臣派人请了美国的专家过来给老爷子会诊。重欢这几日几乎是忽略了小泥巴,整日地呆在医院。
会诊的结果不尽人意。不仅是美国的专家,夜路白和厉暮霭都托人托关系请了海外一些知名专家过来,只是老爷子终究是年纪大了,中风多年,浑浑噩噩,突发急病之后身子亏空,大有油尽灯枯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