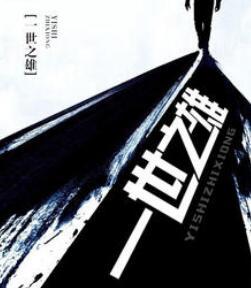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明月不谙离恨苦的前一句是什么 > 第172章(第1页)
第172章(第1页)
>
“不过来了一批人,为首的是一位小女郎,本是可好了,据说杀了不少突厥人,”那人心向往之道,“叫什么齐离弦,小娘子倒也不必害怕,安心休息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的突破口。
枕清没想到在路上还能听到齐离弦的消息,她一直在旁边安静地听着那些人一言一语,只觉得心头微震,好像有股情绪爬上来,旋即又被盖下,脑子一直嗡嗡作响,她恍恍惚惚看向江诉。
“卷柏呢?”
江诉轻声回道:“不是在庭州么?她总是说自己贪生怕死,一辈子要好吃好喝地待在府中,定然不会来这里的。”
不会来就好。
卷柏与齐离弦不同,齐离弦武功极好,善用兵法。
彼时的齐离弦知道自己人数上略亏,只好和突厥在打斡旋战,争取攻心。
突厥半夜入睡却被齐离弦的人马吵闹到精神萎靡,刚想要带着兵刃循着声音杀去,却又不见那些人的身影。白日里困到没有任何精神气,就连拿把刀都有使不上力气的感觉,几番下来,部队顿时感觉疲惫。
在时机成熟的那一刻,齐离弦驾着马匹,率着人马一举攻下那群突厥人后,不料后面有人包抄而来,周围马蹄声四散,齐离弦镇定大呵道:“跑!”
可是那些马匹从四周包抄而来,众人如同被困在网中,四周都是豺狼虎豹,她正打算拼死来开一个口后,抬头突然见到一抹娇小靓丽的女娘身影。
她坐在高大的红棕马匹之上,身后映照无限好夕阳,仿若是这个世间最明媚恣意的女娘。
卷柏高声笑道:“你们这些野蛮子,知不知道我家长史要带着人过来要将你们一网打尽!到时候你么可别被吓得屁股尿流!”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卷柏吸引,齐离弦不自然地握紧缰绳,他们这边是什么情形她自然知道,卷柏这是在诓骗这些人。
那些人也清楚当下的陇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自然没有那么好糊弄,为首的人眼神凶狠凌厉,跟卷柏交锋道:“看来陇右果真是没人,让你这么一个小东西过来,你说人来了,这人可是在那里啊?”
说罢,还要高傲地扬起脖子朝四周看去。
虽说卷柏不是第一次骗人,可是在这群五大三粗的人面前,心不免狂跳,像是直顶胸口,她镇定自若地轻狂道:“你仔细听不就知道了。”
说完,卷柏漫不经心地打了一个手势,顺势还挑了挑眉。
大漠极其安静,只有偶尔来过些许风声,为首的突厥人被日头照得满头大汗,半晌后忽然有些不耐烦,觉得自己还真听这小女娘诓骗。在下一瞬,真的有不少马匹声踏沙而来,所有人的神色一凛,聚精会神地望向声音的来源处。
逐渐看清来人,突厥便自乱阵脚,为首的人当即下令跑,率先朝着卷柏方向驾马过去。
虽然杀不了那些人,但是杀一个卷柏还是绰绰有余。
卷柏自然也发现那群人朝着自己过来,成为一个半包围的状态,其他人又离她极远,已经到了远水难救近火的围困状态,只好夹着马肚朝他们同一个方向驶去,而身后的那群人穷追不舍。
齐离弦见状,心急如焚,当即驾着马匹追了过去,一手执着弓箭,另一只手取下一支锋利的箭矢,将弓弦拉满,毫不犹豫地朝着对卷柏穷追不舍的那人射去。为首那人似有所感,看到齐离弦的样子,随后听着一道厉风扑面而来,带着杀意地刺穿他的肩胛骨。
他露出诡异又残忍的笑容,当即忍着疼痛,跃空而起,飞身坐上了卷柏的马匹。
卷柏感知身后的人,不免睁大眼睛惊呼,她知道现在无论如何都已经逃脱不了,前路是突厥境地,后面是突厥人,而且落在这些人手中必死无疑。
可是要死,也要拉着一个垫背的一起下地狱!
几乎在下一瞬,她就已经决定好动作,齐离弦知晓卷柏的动作,突然觉得胸腔剧烈颤抖,五脏六腑都被颠得生生作疼,喉咙发不出一丝声音。
同道河东逢伊面(七)
“卷柏!”枕清大声一呼,看着卷柏突然伸手,紧紧抓住那人,一同跌落马下。
卷柏耳边有无数摩擦的声音穿过,她好像还听到了枕清的声音,可是卷柏没有管,而是死死抱住这个人。她的身子猛然下坠,碰到地面的那一瞬间,还没感受到撞击的强烈痛感,便有无数马匹从自己身上踏过,她第一次感觉自己像是被踩进了地里。
疼,全身都疼。
枕清呼吸一窒,脸色大恸,手中的缰绳当即一松,心仿若跟着卷柏一同坠地,整个天地都急剧地在瞳仁里疯狂地倒置了起来。
卷柏倒在血泊之中,沙丘上有一条长长的血迹,迎着夕阳,显得无比壮烈,而她手里紧紧攥着突厥人的衣服。
枕清眨了眨眼,眼眶当即泛起了泪水,她趔殂地跑到卷柏的身边,慌慌张张地捧起满身是血的卷柏,满是痛苦:“卷柏,小卷柏。”
卷柏模模糊糊地看着枕清的样子,嘴角咧出一点笑意:“姐姐,原来不是梦,你真的来了。真好,死前还能见到你。”
原本想要抬起手擦拭枕清的眼泪,可是她好像全身的骨头都被马踩断了,她抬不起来了,原来她真的要死了,可是死也不是那么可怕。
“姐姐别哭,小卷柏的手抬不起来,不能帮姐姐擦眼泪了。”卷柏小声道。
枕清知道卷柏这样已经是必死无疑,她即使是神仙也无力回天,她脸色发白,脊背微微弯曲,眼中的泪水却比她先开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