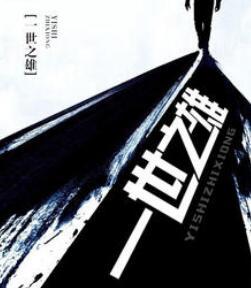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朕靠万人迷保命[穿书 > 第244章(第2页)
第244章(第2页)
他垂头盯着面前被摔得四分五裂的砚台和泼溅一地的墨水,额上渗出了汗。
要是再近两寸,那厚重的砚台砸的就是他的脑袋。
墨汁渐渐浸染袍摆,但他一动不敢动,双手仍高高捧着那饱饮鲜血还来不及揩拭的信物:“侯……侯爷说只要将这个交给您,您就什……什么都明白了。”
条案后立着的人双手撑着案面,胸膛剧烈起伏着,他灼烈的目光落在那掌心中的小小指环上,像是要将托着它的两只手掌都烫出血窟窿来。
剧烈的心跳声中,雍盛的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那枚指环。
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袭来。
他几乎不敢靠近它。
“你说你……刺了他一剑?”他反复确认。
狼朔简直要疯了,一遍又一遍解释:“是,是侯爷自个儿撞上来的。”
这锅他是真不敢背,一旦背了人就没了。
房内一阵静默。
“为什么?”雍盛歪头问。
方才发过火后,他就离奇地镇定了下来,但眼睛瞪得很大,额角青筋迸起,看起来更可怖了。
狼朔崩溃:“臣也不知,当时事发仓促,臣措手不及,待反应过来时,这剑就已经……”
他指着横放在膝前的剑,剑尖两寸与血槽内皆是干涸的血迹。
雍盛走过来,弯腰拾起剑,细看那森森剑锋,斑驳剑身上映出他阴郁的眉眼。
他往下轻轻一挥,“嗒”,长剑就架在了狼朔颈边,惊得狼朔浑身一颤。
“这剑若这般砍下去,约莫很疼吧?”
他如此发问,倒像是当真好奇,可明明是毫无起伏的声线,听来却那般惊悚骇人。
狼朔浑身透凉,汗如雨下,咬牙低头:“臣办事不力,罪该万死,还请圣上责罚!”
“咄”的一声脆响,长剑移了开来,剑尖磕在地上。
雍盛垂手拖着剑,漫无目的地踱步,剑尖与地面蜿蜒摩擦,划出刺耳的声响。
“在他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境况下,你们也未能将人成功带回,而是任由不速之客将其劫走。”
狼朔急切道:“对方玄衣赤笠,训练有素,多半就是此前销声匿迹的赤笠军,此番来势汹汹,熟知地势地形,且无意与我们多作纠缠,掳了人就分作几路四下逃窜,属下无能,竟追丢了。”
“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