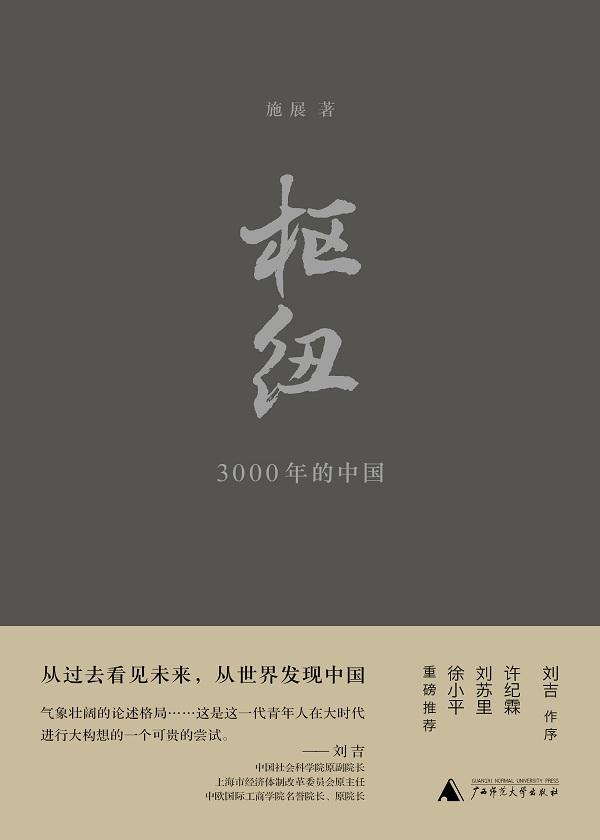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姝色难逃娄华淑 > 第八十九章 云霄可凌(第1页)
第八十九章 云霄可凌(第1页)
窸窸窣窣,顷刻之间,帷帽上已经落满了各色的花瓣。“画琴,接着!”只听到一道耳熟的声音,响在一臂之外的距离处,带着兴奋之意。这是……晏崇钧的脚步,几乎是下意识地往那个方向挪动了几步。人潮更挤了。“别动!都别乱动啊!”“这儿有人!”“刚刚谁踩到了我的脚?”一大把凌霄花,灿然而坠,被他兜了个满怀。他怔然抬头,捧住这片从天而降的惊喜,入眼是旋薰金缕,彤蕊若烧。“我的花!”翠蔓红芳后,露出一张焦急的小脸。被身后的人潮一挤,被迫往前一踉跄。“——小心!”晏崇钧连忙扶住她的胳膊。隔着朵朵盛放的凌霄花,和垂下的轻帷,两个人在拥挤人群里对视上。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花是他喜欢的花,人……“这是你的花?”“……是,多谢公子。”薛鸣佩好不容易从掌花娘子那里,得了最中意的这么一捧凌霄花,正要扔给等在一边的画琴,免得花在拥挤中毁坏。谁知道,却失了准头,打在了一位陌生公子身上。那人戴着帷帽,一身粗服,容颜被大把的凌霄花和轻帷遮住,只能隐约看见个高挑劲瘦的身形。她若有所感,眉头微蹙,还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却愈发挤了。“抱住,可别再丢了。”嘈杂人声中听到这一句,便觉得手上一重,那凌霄花被推回了自己怀里。“姑娘——让一让啊!让一让!”“哎呀你这个人挤什么啊!等着投胎呢!”“骂谁啊兔崽子!”周围乱成一团,薛鸣佩只来得及接稳花,就被画琴半护住,焦急地往人潮涌动的方向拉去。“佩夫人,快!好像有人打起来了,别往那儿走,小心些!”等到她褪去狼狈,再抬起头来张望,哪里还有刚刚那人的影子?“佩夫人,您看什么呢?”“……”薛鸣佩不死心地又往其他方向看了半天,最后低下头来,拨弄了一下怀里的凌霄花,“没什么,走吧。”应该就是个不认识的路人?可是,总是莫名地有些在意……香车高台上,一个人不知道何时,便站在了细挑的尖顶台座上,俯身望去。密密麻麻的人群,攒动的人头,什么也分辨不清。他却笃定地遥望着一个方向,久久沉默。半晌,摊开掌心,露出一朵凌霄花来。不告而取,是为窃也,愧哉愧哉。怪只怪这花生得实在太合他的心意,明知道花有其主,却还是放之不下。最后只能偷偷摸摸地撷取下这一朵来。实在是无耻之尤。他轻叹一声,一边骂着无耻,一边低下头来,在花上轻轻落下一吻。香台下。“……”小红仰面,露出个恨不得以死明志的表情。他那个想一出是一出的主子,怎么突然又跑到那上面去了!显摆他轻功是吗?还是犯了什么毛病,想从高台上跳下来?不行不行,今晚回去以后,得合理分配一下,该怎么和侯爷告状,让世子爷少犯点病了!月色如华。临风院的厢房,薛鸣佩将那一大捧凌霄花换了水,养在玉瓶里,只觉得原本有些暗沉的屋子,都被这鲜亮之至的颜色给映亮了几分。连原本摆在一旁的鸳鸯茉莉,似乎也逊色起来。今日去看了娘,发现她病情果然好了一些,又让馥恒庄趁着孟夏花期说成了几件大单子,还得了合心意的花。凝滞在心头数月的郁气,似乎都倏忽消散了。这一夜,薛鸣佩难得酣睡,沉眠无梦。很快,几个月过去了。转眼,戚韫和温盈的婚期也越来越近。这些时日,戚府的人虽然明面表现得不明显,但望向薛鸣佩的眼神,都多了些深意。尤其是见二公子为了婚事,一头栽进去尽心置办,几个月忙碌,跑东跑西,一副极为重视的模样,许多人打量薛鸣佩的时候,更多了分讥诮和怜悯来。“早就说了,二公子不过是一时被她勾引罢了,怎么可能真把她放在心里?”“是啊,这才几个月,听说二公子就看都懒得看她一眼了。等到郡主入了门,她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呵呵,以前我就看不惯她那个轻狂样子,还爱在男人面前装模作样,呸!最好让她……”“嘘!你小声点!你忘了戚霜她们的下场了吗?”一开始,薛鸣佩听了只当没听到,到后面,见这些旁支的人愈发得意,一副温盈马上就为民除害的痛快嘴脸,干脆直接站了出来。“这位……是西头三房的七姑娘吧,刚刚说了什么?我站得远,没听清。要不,你再重复一遍?”几人面面相觑。说得太忘情了,落到当事人耳朵里,尴尬。本以为薛鸣佩正自顾不暇地烦恼,肯定没心思和她们掰扯,谁想到她竟然直接当面问出来了。“没什么,没说什么……”“你们怂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一个性子傲些的,横了薛鸣佩一眼,“要我重复,那我便重复呗?姐妹们就是关心你,听说外面人家,正妻过门后,这做侧室的都得第一时间过去好生伺候着。但郡主身份尊贵,怠慢不得,比起一般人家的主母更加不同。薛姐姐,你准备好怎么伺候好郡主了吗?要是不会,姐妹们倒是有时间,去给你打听打听。”有她开口,其他众人也褪去了原本的一丝担忧,齐声嘲笑起来。“我可听说,侧室是要给正妻布菜的呢。”“何止啊,东陵那边的规矩,侧室还要给夫人脱履捏肩,端茶奉水,新婚夜还得在房门外伺候着,主子一有需求,就得进去上前听命……”“哎呀呀,原来这做侧室,有这么多规矩啊,我孤陋寡闻,竟然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也正常,咱们姐妹生来就是被府上人当后宅主母精细养着的,所以在族学中又学诗书礼仪,又学理账管人。不像有些人,没有做正室的好命,便只好挖空心思,去学些狐媚之术啰!”女娘们一声一声,见薛鸣佩被说得沉默,脸色苍白,笑得愈发肆意畅快起来。她们笑了好一会儿,见对面却寂然无声,那笑声便滞涩迟疑起来。“说够了吗?”薛鸣佩静静地望着她们,然后回身看向画琴和枫儿,和廊前清扫的下人,“你们也都看见她们了?”“……”薛鸣佩搞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