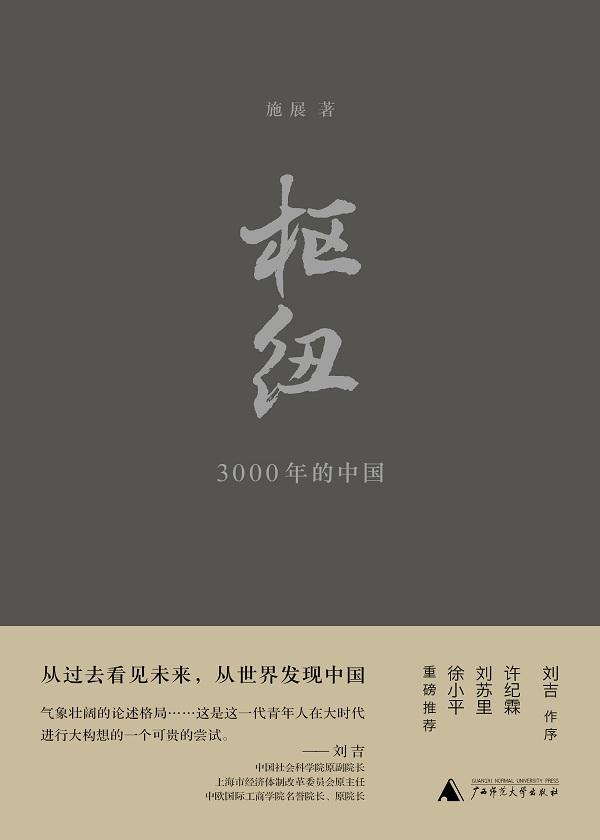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姝色难逃娄华淑 > 第四十二章 父女重逢(第1页)
第四十二章 父女重逢(第1页)
馥恒庒的会客雅间。路得济按照薛鸣佩吩咐的,备上了上好的吃食糕点。说实话,其实他不明白,为什么小姐再三强调,这一次江南的商人来了,一定由她亲自招待。他自觉是小姐的乳兄,又为她打理铺子,还是个成年男人,这种场合出面,比小姐更加合适。但是薛鸣佩却十分坚决,还肃然直言这件事情关系到铺子未来的存亡,自己绝对不可自作主张。“……”想到小姐接手馥恒庒的生意之后,几次重大举措下来,铺子的流水直接翻倍,路得济还是闭了嘴照办。可是他没想到,这江南派过来的管事,竟然这样不晓事!言辞磕磕绊绊就算了,竟然一直盯着他们小姐不转眼?要不是小姐说这桩生意重要,又没有出言,不好莽撞行事,他早就沉下脸把人赶出去了!“郑管事,这是江南的茶叶,你……”“路大哥。”薛鸣佩笑了笑,“你先去忙吧,正好我十分好奇江南生意的现状,想请教这位管事,独自聊聊,有什么事情我喊你。”“这——”这怎么行!路得济变了脸色。他们小姐一个还没有出阁的女儿家,怎么能单独和一个刚见面的中年男人共处一室?即便是大白天,那也是大大的不妥。“路大哥。”薛鸣佩的语气有些冷了,“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小姐醒过来之后,一直待人亲善,和路得济共事得也很愉快,以至于他忘记了,以前的小姐的是什么样的。路得济变了脸色,眼中划过一丝惊恐,仿佛是回想到了什么可怖的事情,连忙低下头应下:“是,是。”出去的时候甚至亲自关上了门。没了其他人,郑锡年哪里还按捺得住,立刻站起身,脸上胖嘟嘟的肉都跟着抖了抖:“这位——这位小姐——”他望着这姑娘的身形,语气变得迟疑。身量比他的佩娘矮了一些,也瘦上一些,可是,可是那份货单,还有多出来的四个字……下一刻,他的后话停在了唇角,眼睛瞪大成了铜铃。薛鸣佩一把扯下幕离,蓦然跪下。“爹!”“是我……佩娘……”她仰起脸,眼睛比兔子还红,本想忍住。可是在这个人面前,所有积攒的委屈、害怕和狂喜,都再也抑制不住得喷发出来了。爹……她终于见到爹了!……一刻钟后,郑锡年依旧是没有反应过来的怔愣样子,无法置信,犹犹豫豫地抓着薛鸣佩的手,像是第一次认识她似的,不断打量,口中不断呢喃。“这是真得吗?”“我不是在做梦吧?”“佛祖,菩萨,玉帝,阎罗王……”他呆呆地把九天神佛,中原的外乡的神仙全都念了个遍,末了陡然往自己脸上狠狠来了一下。巴掌响得差点惊动了外面守着的仆从。他的佩娘,竟然没死,重生在了另一位小姐的身体中?这小姐……和他的佩娘生得可真像啊。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离奇的事情?简直像是说书先生们嘴里的话本子似的。真得不是有人找来这么一位,故意哄骗他的吗?……即便这是一场骗局,是有人要借此骗取他郑家剩余那点薄产,他也、他也甘之如饴了。只希望对方能够骗他骗得更久些。佩娘的尸体,是他亲眼看着官差打捞上来的。才十六岁的女娃娃,他和青娘从一个奶团子,千娇万宠着,才养到这么大。成了一个有胆色又孝顺的好孩子,站在那里,意气风发的,街坊邻居谁家不羡慕他老郑?几天之前他和青娘说起女儿的亲事时,还痛骂不知道哪家的浑小子,才配得上他这么好的女儿。一转眼,却只看到她被捞起来,浑身冰冷地躺在船上,无论他怎么撕心裂肺地哭喊,也不肯睁开眼睛看他一眼。身上那道伤,直接贯穿了她的胸口。她那时候,该有多痛啊?郑锡年像是陷入了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那之后几个月,每天都枯坐在女儿的房间里,犹如行尸走肉。然后再不死心地一次又一次去官府衙门,不断地送银子,不断地问那些水贼今天追到了没有。得到的却是越来越敷衍的回应。……直到上个月,曾经在他们郑家做事的徐家老四,把一封从京城寄过来的信交到他的手上。“佩在京城”。看到信的那一刻中,他就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的癫狂,浑身上下犹如烈火焚烧,抓心挠肺,恨不得立刻飞到京城去查个究竟。一会儿异想天开女儿是不是没死,陷入一家团圆的美梦,一会儿又像是重新摸到了女儿冰冷的尸体,陷入愤怒中。佩娘已经死了!尸身是他亲手收殓埋葬的……到底是谁!是谁!竟然用这种事情戏弄他一个父亲!等他找到这个人,绝对不会放过他!可是……可是也许是佩娘曾经留下了什么东西呢?这样度过了十几个辗转反色,夜不能眠的日子,他马不停蹄地带着商队来到了京城。身为商人的谨慎,让他意识到,对方如此隐晦地寄来这么一封语焉不详的信,不一定是为了吊人胃口,也可能是因为对方的处境不妙,受到诸多限制,只能这样传信。哪怕只有一线可能,万一对方是和佩娘结有善缘的人,他也不能贸然行事。于是,兜兜转转,最后以这么一个身份,找上了馥恒庒。可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真得还能见到女儿,还听到了这么一番解释。“爹?您这是做什么?”看到爹还是这么个老样子,惊讶激动到极致连自己都打,薛鸣佩又是好笑又是难过,连忙把人的脸掰过来看,心疼地揉了揉他打出来的红印,语气无奈,眼睛却湿润。“是我,爹。”她轻轻地,一字一句道,“我真得回来了,我没死。”郑锡年的嘴唇剧烈颤抖着,哽咽难言。半晌,只吐出了一句话。“佩娘,你受苦了啊……”只有她的爹娘,明明自己遭受诸多苦难,知晓她的身份后的第一句话,却不是追问,而是心疼她。薛鸣佩这才发现,才不过半年时间,爹竟然多了这么多白发,像是突然憔悴苍老了十岁,走路的时候一只脚还不利索起来。与亲人重逢的喜悦淡去,薛鸣佩心中刺痛。“爹,您、您怎么变成这样了?娘呢?她怎么没有跟着一起上京?还有大哥!他在西边传信给你了吗?”收到信以后爹立刻过来,没道理娘还有耐心留在江南。以她的性格,怕不是比爹更加急迫知道真相。她心头涌上了剧烈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