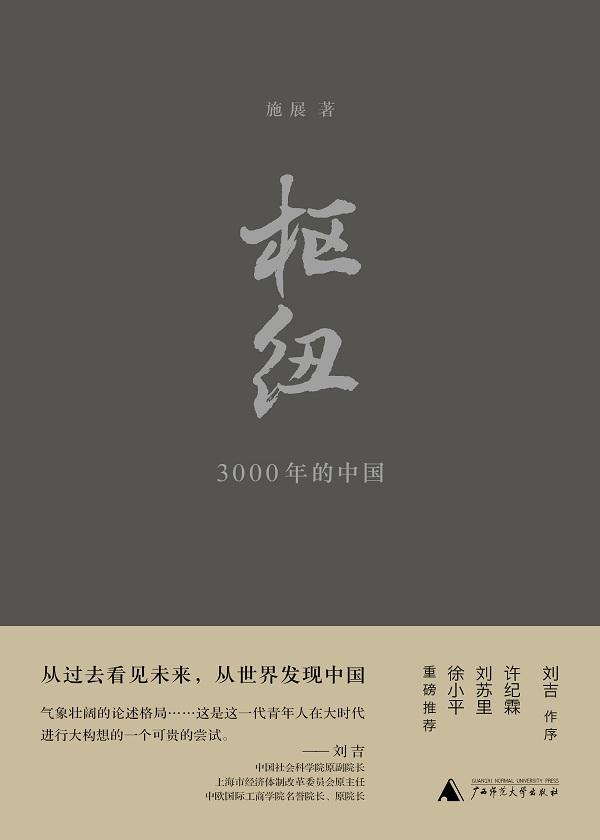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挚欢璀璨啊 > 第32章 难伺候(第1页)
第32章 难伺候(第1页)
他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裸露出的地方遍布伤口。
打眼看去。
有刀伤,也有枪伤。
皮肤透着失血过多后的苍白。
温瓷压下心中惊讶,对傅景淮道:“他这种情况,应该送医院救治。这里条件达不到,伤口就算缝合了,也很容易感染。而且,他出血很多,可能需要输血。”
傅景淮回:“他不能去医院。”
又说:“需要什么,你告诉我,我来想办法。”
傅景淮说不能去医院,一定有原因。
温瓷没多问。
用最快速度,检查了一遍男人身上的伤。
也不知该说他运气好,还是运气差。身上二十几处刀伤,多处枪伤,竟没有一处致命。
伤他的人不是冲着他命,而是凌虐。
又或者,拿他的身体当筹码,为了达成某种条件。
这些不是温瓷该问的。
她写了治疗需要的消炎药和止痛药,还有包扎和后期换药需要用到的纱布,让傅景淮安排人去买。
从药箱拿出麻药,给他注射。
等他昏睡过去,开始着手处理枪伤,取弹头,然后清理创口,缝合。
得益于这几天割了又缝,缝了又割的生猪皮,她手法又快又稳。
傅景淮拿了把椅子。
在旁边坐着看。
女子戴了口罩,巴掌大的小脸被遮住大半,露出一双秋水浩波般,明净的眼睛来。
眼神认真又专注。
她手上戴着医生才用的胶皮手套,动作娴熟,他忍不住想起,那双手帮他上药时的情景。
她指尖很细。
很凉。
落在他脸上时,有种酥酥痒痒的触感。
可就是这样一双手……
开枪,动刀,好像没什么不会的。
他禁不住有点儿好奇,温树声一家子都是文人,怎么生出来一个枪法这么准的女儿?
温瓷在埋头苦干。
没留意到傅景淮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