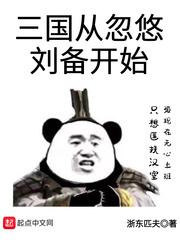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乡村阴阳师大结局 > 第159章 内口(第2页)
第159章 内口(第2页)
我一愣,心说衣裳没坏,你瞎缝什么玩意儿?
要是练习女红,也不至于在新买的羽绒服上练啊,那得多败家?
我正要批评白玲两句,就看到她低头咬断了线头,而后把旁边的那一沓钱,一张一张的叠成小方块,往她羽绒服兜里揣。
我这才瞅明白,俺妹子到底是在干啥。
她把里兜缝了一大溜,只留出个很小的口子来;那些票子叠成的小方块,就顺着这小口子,慢慢都塞到了里面。
做完这些,白玲乐呵的拍了拍羽绒服,“这下好了,不用再担心丢钱了。”
我一拍脑壳,心说麻蛋,俺妹子总给我制造惊喜:她把羽绒服里兜,缝的狗齿狼嚎的,就是生怕会丢钱。
这……这也太在意钱了吧!
白玲把我弄得哭笑不得,想了想,我干脆把要说的话都憋在肚子里。
人家都缝完了,我再崩(批评)她还有啥用?闹不好,还得惹得白玲盯着我一顿瞅,最终投降服软的,还得是我。
我从炕柜里掏出《阴阳》,脱掉棉鞋上了炕;旁边,王娅正斜不悠子、撅着屁。股趴炕上写作业。
看着她那圆了咕咚,我就不由得想起了今儿个清晨的事儿,一时手欠没忍住,照着圆了咕咚就拍了一下。
“二丫,好好学习啊!等你将来考上大学了,哥送你一辆蚂蚱子(拖拉机)当贺礼!”我一本正经的说道。
这一拍不要紧,王娅立马就炸庙了,从炕上爬起来,跟我撕撕巴巴、非要挠我脸。
这给我吓得,赶紧用胳膊肘子护住脑瓜子。
我说王娅你别发疯,哥那是逗喽你玩儿呢,可别忘心里去。
我心里却有些奇怪,这刚拍下屁股,她就炸毛了,那早上时候呢?那会儿,我都给她蹂成那样了,她咋不说要挠我?
这些小娘们的心思,真特么难猜。
王娅跟我武武宣宣好一会儿,到底在我左脸蛋子上,狠掐了一把,这才消停下来。
我疼的呲牙咧嘴,嘟囔道,“死丫头片子,下手这么黑!我改主意了,就算你考上大学,我也不送你蚂蚱子了。”
王娅“呸”了一口,又剜了我一眼,说道,“好像谁稀罕似的!等俺考上大学,指不定在哪个大城市里念书呢!”
“到时候,人家同学都坐着轿车或者公交车去学校里报道,就我自个儿,开个蚂蚱子突突突、冒着黑烟进大学校园?郭哥,你脑瓜子是不是让门弓夹了?”
我让王娅说的老脸通红,想要反驳几句,又觉得她说的在理。
艹的,我就是随口逗咳嗽而已,哪想得到,开蚂蚱子去大城市,会那么丢人?
在俺们村儿,像苟村长那样,能开上蚂蚱子的,就老有钱了;我是真没想过,要是拿去跟城里人比,苟村长家那点儿钱,屌。毛都不算!
我揉了揉左脸蛋子,不再逗喽王娅,翻开《阴阳》,直接找到了阴物篇。
没翻几页,我就看到了一段关于虫子的描述。
瞅了几眼,我不由得猛拍了一下大腿。
妈了巴子,我说看着那白色虫子,总觉得有些熟悉呢。
这白色虫子、苟子谦尸体后背的那黑蝴蝶图案,都特么有关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