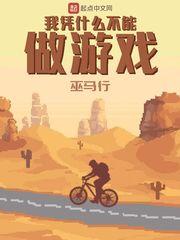笔下文学>主母在上打死妾室 > 第两百零二章 王爷害羞了(第1页)
第两百零二章 王爷害羞了(第1页)
谢景辞的一双眼目光落在苏映安纤纤玉手拿着的珍珠项链上。这珍珠很好,但形状不一。难不成她不喜欢这种异形的?他抿了抿唇,点头:“是。”苏映安闻言粲然一笑:“我最喜欢这种形状各异的珍珠,只是做成了项链,便要从中穿孔,难免会破坏珍珠完整性,我还是更喜欢洒在玉盘中的珍珠,在蚌壳里面的最好,野蛮生长很独特,又有自己的个性。”谢景辞微微一愣,盯着她把玩珍珠的模样,有些出神。苏映安身上的独特才是最难能可贵的。他不自觉被吸引了目光,久久移不开了。等屋子里面静下来之后,苏映安才抬眼看向了坐在对面的人。两人目光相撞,仿佛这一刻什么都暗淡了下来,只有他们能清楚看见对面的模样。苏映安最先回过神,抿唇垂眸说:“时候不早了,王爷也已经将东西送来了。”这是在下逐客令了。谢景辞的眼神还是看着她,“那我明日再来。”她蹙眉说:“王爷没事还是不要再来了。”谢景辞扬眉,还振振有词道:“我作为客人,来茶饮铺子,有什么问题吗?”苏映安顿了顿,她语气也变得轻松了起来,因为她以为谢景辞会因为自己说的话而生气。“可是王爷,这茶饮铺子,虽不曾挂只为女客供应,但实际上,来我铺子的人全是女客。”她说话的时候,嘴角上扬,连带着声音都上扬了一些。谢景辞的心再一次荡漾,连背心都有些发热了起来。他轻咳一声:“或许我去画舫,不算什么错。”“明日我不一定要去画舫。”谢景辞又说:“这样……”苏映安见他还想说什么,立马制止道:“王爷,时候真的不早了。”谢景辞起身,合上了折扇,折扇上吊着的玉坠,轻轻晃动。她看见,惊诧道:“王爷不是说那玉佩坏了吗?”谢景辞低头看了一眼,轻勾唇角道:“是,修好了。如此,我便告辞了。”苏映安道:“诶,王爷,那能不能将玉佩还给我……”还没说完,就见他身影已经闪出了屋子。他好像是在逃避什么。苏映安嘴角一抽。绿枝从外面进来,疑惑道:“小姐对王爷说了什么?他竟然是红着脸跑出去的。”苏映安闻言,笑出声音:“原是觉得丢脸了,才这样跑出去了啊。”绿枝一头雾水。次日,苏映安一早便出门去了画舫。绘椿看见她还有些惊讶。“小姐怎么来了?还以为您这几日要忙着清点小院的东西呢,我今早出门的时候,就看见小芹和两个丫鬟去恒园搜罗您遗落的东西了呢。”苏映安揉了揉鼻子才说:“好久没来画舫了,来看看。”她也说不清,兴许是因为昨夜谢景辞说的那一句——那我明日去画舫。真是鬼迷了心窍。只是来都来了,苏映安也不能因为反应过来自己因着谢景辞一句管同样的话,便去了画舫里面做事了。因着她跟侯府的关系,苏映安本以为画舫的生意多少会受一些影响。谁料绘椿将账本拿出来了的时候,惊呆了她。“昨日这么多人来?”“可不是,连备用的小画舫都摆上了两桌,吟风去那小画舫上弹琴的时候还战战兢兢的,生怕船翻了呢。”苏映安笑说:“我就说,客人里面也不过是小部分人因着侯府人脉而来,其余的客人,都是我自己的客人。”绘椿点头,又有些担忧道:“只是昨日我听说厅中不少客人都在讨论小姐跟侯府的事情呢,说的话并不是那样好听。”苏映安却眼睛一转道:“很不好听?多数是批评我的吧?”“倒也不是,就是一些男子,好似高高在上,说你离了侯府日后过的不会像是一个人样之类的话,总之太难听了!”绘椿说着,便嫌恶地皱了皱眉头。苏映安扬了扬眉毛说:“他们觉得我没有了男人,便不好活下去了吧。”绘椿都想吐了:“那些男人,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模样,难不成小姐休了陆世子,还能看上他们不成?”她却很是平静地说:“正好,那就利用他们,再好好演一场戏吧。”绘椿不解:“小姐不生气他们说的那些话吗?”“生气?那岂不是正中他们下怀了?不生气,他们会说我强装镇定。怎么做,他们都会往我的头上泼脏水,与其用苍白无力的语言去自证,倒不如借此机会让侯府名声更臭一些。到时候可怜我的人是他们,骂侯府的也是他们,被蒙在鼓里的不还是他们这一群蠢货吗?”苏映安的话很有力量,绘椿都听得笑出了声音。只是在画舫上忙碌了一整天,苏映安都没有看见谢景辞的身影。绘椿见她总是在画舫停靠码头的时候,朝着码头方向张望,便上前问道:“小姐可是在等待什么人?”苏映安收回目光,摇摇头说:“没有。”她有些失望,总觉得自己的情绪像是被谢景辞牵引,偏偏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负责人的,说的话也没有应验。王府。下午光景。谢景辞刚伏案办完公务,便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他搁下笔,揉了揉鼻梁才说:“进来。”来人是王府的侍卫。侍卫抱拳道:“王爷,府外有一名自称捡到了王爷玉佩的女子求见。”谢景辞脱外衣的动作一顿,很快便换上了自己的常服,快步往外走去说:“人在哪儿?”侍卫知道王爷最近一直都在找玉佩这件事情,跟在他身后说:“已经请那位姑娘进了花厅,现在就在花厅等待王爷呢。”谢景辞没说话,只是脚步更加快了一些。看见王爷如此,侍卫眼神却有些隐隐担忧。王爷若是看见手持玉佩的姑娘,会不会失望呢?他不知道的是,自家王爷此时内心无比期待。而谢景辞期待的脑袋里面,那张脸是相当具象化的模样。那张脸,曾出现在他的面前无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