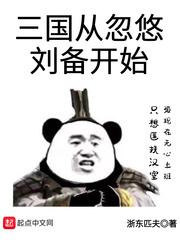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就像他父辈和祖辈曾经的模样歌词 > 第82章 周刊(第1页)
第82章 周刊(第1页)
那年5月,怀斯特至少给德莱克斯勒写了二十多封信,甚至有好几次都亲自跑到他的面前,苦口婆心的劝他。
他甚至是“狗急跳墙”,十分严肃的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作为辣脆党的创始人,却没能成为辣脆党党魁的原因了。你表现得犹豫不决,太过保守,醒醒吧!你应该知道自已想的是什么,你要反对!反对!阿道夫出卖了你!你要反对他,严格管控他!”
他抓着德莱克斯勒的肩膀,抓狂的摇着他,仿佛要将自已的决心传递给他。
怀斯特并不擅长劝人,往往说着说着自已就像急起来。但是,他却觉得自已的真挚是无与伦比,顶多就是要些时间理解罢了。
德莱克斯勒沉默一会,才说:“给我几天时间想想吧。”
“好,”怀斯特放开了德莱克斯勒,“我一个星期后再过来。”
在德莱克斯勒考虑的时间里,地下辣脆党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了。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敌对的双方有时候竟然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在乎这样做带来的损失。
得知这个消息时,怀斯特正在用餐,不过他仍然决定“放下自已的午餐,给德莱克斯勒写一封信”。
他声称,那些大打出手的人为辣脆党的荣誉带来了损失,也给他们送来了更多的丑闻。为了减少这些丑闻让党派回到正轨,他们就必须对党进行彻底的改革。
6月,德莱克斯勒终于是给了怀斯特答复,表示愿意对辣脆党进行改革,“严格管控阿道夫以及其他危害党派的人。”
然而,德莱克斯勒这次的答复却在不经意间闹出了一些丑闻。有人说,德莱克斯勒虽然反对阿道夫,但并不至于到“撤他的职”的地步,而怀斯特的战略很明显是“让他当一个普通党员”。
这些阴谋论者猜测,德莱克斯勒是遭到了威胁,所以才会同意改革。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可以确定的是,怀斯特已经为他第一步的“肢解辣脆党”奠定了基础。
汉弗里克可没心思参与怀斯特“肢解辣脆党”的计划,他一门心思的“搞演讲”“写著作”。
他写的是自已的自传,名叫《我与德国》,第一卷的题目冗长,叫《19世纪末的新生儿,15年来的快乐、悲伤、愚蠢、谎言》——第一卷的时间从1899年到1914年,详略得当的描写了汉弗里克的童年,在波茨坦的岁月,以及父母去世的悲痛。
关于童年的岁月,汉弗里克是不做任何修改,他做了什么,就在里边写什么,毫不掩饰。
戈培尔看过汉弗里克的手稿,问他打算在那15年里付出多少笔墨,汉弗里克答道:“很快,我可能一个月就把我的童年生活搞定了。”
汉弗里克的警卫魏格伦·巴勒斯特回忆说:“他每天写一部分,写完之后,便给我和办公室内的其他同仁们阅读,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需要润色的。”
这本书并不是在卧室写的,相反,他一直把手稿放在办公室和书房,从晚上9点写到次日凌晨1点(通常都是这个时间)。
他似乎并不担心自已的手稿失窃,毕竟魏格伦除了保护汉弗里克的人身安全,还要保护他的手稿不被偷窃。
“但是偶尔,先生也会带着他的手稿到《人民观察家报》去,用那里的打字机,双手就像是弹钢琴一样的打出字来。”
去《人民观察家报》的路上总是显得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