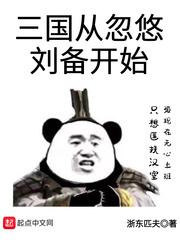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白热永恒是什么意思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
“梅林啊,上帝啊……难道全英国,只有我知道未来会如何吗?邓布利多又是什么意思,那个挂坠盒到底有什么作用?”
长久待在这里,耳边响起羊皮卷上邪恶的诅咒,查理·唐森家那种令人窒息的眩晕感归来。她扶着书架,站起来,有气无力地拉开书房门。
门外是熟悉的黑影。
雷古勒斯提着一盏油灯,发尾因打湿而微微上翘。他显然无暇打理,因为他另一只手提着一双麂皮高跟鞋,等待着她。
他的眼睛躲在黑暗里。
“晚上好……很高兴看到你还活着。”她搂了搂他,没头没尾地说。
他嗅到她身上的酒味,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她的包丢在楼梯间,蛋黄色的睡裙露出一角,无名指上戴着戒指。
“晚上好。吃过晚饭了吗?”
他的手掠过她的侧腰。她出门前,他重新系紧的蝴蝶结,还在那里,没有人解开过它。立刻有条快乐的河流在他心中汤汤流着,比较之下,那条塞满阴尸的暗河就像小水沟。
“正想去吃,”她恹恹地,顺口问道,“你刚才也出门了?”
“以为你不回来,所以去了一个地方。”他说。
凯瑟琳醒了。直觉告诉她,他身上的寒气来自于那个岩洞。
雷古勒斯是什么时候死的?她隐约记得,就是在十几天后……是的,他死去的时候,夏天才刚刚开始。
“我说过只是出去玩玩,”她神经的弦勒紧,“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不回来?”
雷古勒斯反问:“你为什么带走了睡裙?”
凯瑟琳被问懵了。英文词语一个个滑过喉头,怎么选?最后她选择了承认。
“是的,我是有那么一瞬间,觉得今晚可能不会回来,”他的手收紧了,她感觉得到,“……但我还是回来了。”
“如果我今晚真的不回来,会怎么样?”
“什么也不会发生,凯瑟琳,”他眼底有深洞,有刚刚夭亡的赴死之心,“你渴望拥有的一切,我都不会带走。”
他们走到餐厅。凯瑟琳注意到烛光。今晚有甜奶油蛋糕、朗姆酒和蜡烛。
没人唱生日歌,他们都觉得这首歌蠢透了,每一个音律都彰显着只有小孩才能欣赏的蠢气。
凯瑟琳切开蛋糕,拆吞入腹。她饿极了。蛋糕坯夹着苹果馅,酸甜中含有百分之三的止渴剂。她吃到一半,又喝了朗姆酒,胃里才暖和。看电影太消耗体力了,更别提她的未来完完全全是一部惊悚电影。
吃了一牙蛋糕后,她突然抬头对雷古勒斯说:“我应该戒酒。”
过了一会儿,她又自怨自艾般改口:“我是酒的奴隶,我是个天生的酒囊。”
“没有什么应不应该的,”他今夜有种超脱生死的气质,“酒不是人,它不会毁了你。只有人才会毁了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