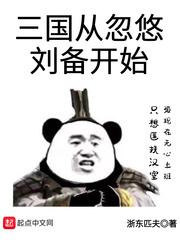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国公府的二小姐毁容后 > 第110章 他爱极了我(第1页)
第110章 他爱极了我(第1页)
桑晚被带至一个废弃的货仓,缚在一根木柱上,不得动弹。
一顶软轿随后落下,孙妈妈挑开轿帘子,嘉宁县主从轿子里施施然走了出来,满眼得意。
“牙尖嘴利的,这会子怎么不叫了?”
桑晚冷哼了一声:“深夜掳我至此,眼里可还有王法?”
嘉宁县主丝帕掩唇,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你一个卑贱如泥的人,也配同我谈王法?天家就是王法。我是官家最宠爱的容妃的亲妹妹,我就是王法!”
她走近桑晚,捏住了她的下巴,双目淬着怨毒:
“在裴府那日,我就想挖了你这双眼珠子!你算什么东西,竟成了谨之哥哥的枕边人。”
桑晚瞧着她,笑得不阴不阳:“你拢不住裴谨之的心,朝我撒什么气。”
嘉宁县主恼羞成怒,扬手一个巴掌,桑晚避了开,但发髻被打散了。
黑丝如瀑布散落,别有一番破碎的美,越加惹人嫉妒。
“我让你得意,今日本想一刀捅死你,现在我改主意了,贱人,我定是要让你尝尽苦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有什么本事,使出来,让姑奶奶看看。”桑晚嘴硬得很。
嘉宁县主受不得刺激,攥着她的衣领:“贱蹄子!就是你坏了我和谨之哥哥的婚事。若不是你横插一脚,我与他早就奉旨成婚了!”
桑晚笑得更大声了:“奉旨成婚?当初裴老夫人跪着求你的时候,你倒是答应啊。”
“你,你怎么知道?!”嘉宁县主涨红了脸。
“你不仅不答应,还谎称没有赐婚旨意。”桑晚啐了口唾沫笑道:“让我猜猜,你为何如此生气,那旨意去了哪?啊,想必是撕了?烧了?还是狗吃了?!哈哈哈哈!”
否则依她的脾气,早就拿着赐婚圣旨来闹一番了。
“那是本县主不稀罕!那病秧子迟早要死的!天下好男儿多了去了,如今是我不要他!只不过,本县主不要的男人,你也没资格染指!”嘉宁县主被说戳中痛处,气得吐血:“拿鞭子来!看我不抽死她!”
侍从递上了软鞭子,嘉宁县主洋洋得意地甩了甩,试图在桑晚的脸上找到恐惧和臣服。
“病秧子?哈,你怕是不知道裴谨之有多厉害呢!靠过来,我告诉你。”
桑晚笑得邪魅,这笑中还带着得意,这让嘉宁县主想起那一日她左肩的牙印,妒火上身,果然靠了过去。
二人几乎面贴着面,桑晚一双眸子映着火把的倒影,流光闪动:
“世子爷身子骨强得很,夜夜都要,每晚少时两三次,多则一夜七次。他爱极了我,恨不得死在我的身上。哈哈哈哈!”
桑晚疯了似的大笑,眼里满是挑衅。
“贱人!你这个贱人!”嘉宁县主气疯了,揪起她的头发就往柱子上撞。
可桑晚的头还没撞到柱子,嘉宁县主的手却顿在半空,如同被人点了穴。
“我……我的手……额……”
她四肢僵硬,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整个人像一根木头似的,直直地栽倒在地上。
“县主,你怎么了?”秦嬷嬷惊得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