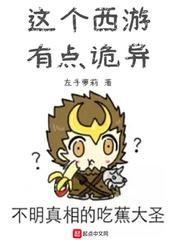笔下文学>寒门贵子百度百科 > 第八十五章 迨其谓之(第1页)
第八十五章 迨其谓之(第1页)
这一顿茶吃了快两个时辰,满屋的茶客先是聒噪起哄,慢慢的归于无声,一个个聚精会神的听周七巧讲述这条白蛇的故事。??人间有爱,妖亦有情,五百年轮回不止,沧海桑田,水枯石烂,可救命之恩却没齿不忘,相识断桥,相知雨后,历尽劫难,终成眷属,这一曲人与妖的恋爱,仿佛比之秦汉以来所有的爱情故事都要荡气回肠,让人潸然泪下。
周七巧口干舌燥,但看着钵盂里的钱慢慢堆满了出来,心中的爽快实在无以言表。徐佑之前跟他们承诺过,说书过程中收取的钱财全归他们所有。也就是说,除了每日五百文的固定收入,还有额外的这些赏赐可以纳入囊中,只看今日茶客们的反馈,粗略估计一下,纵然没有五百文那么多,也相差不是太多了。
这时候他才记起去找徐佑,可四周望了望,没见到人影,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一行人已经悄然离开了。
同样离开的还有韩七,他听了小半个时辰,虽然觉得很有吸引力,但起初跟李福的争执吃了亏,心里一直不满,这种不满也延续到了说书人身上,起身走到门口,骂骂咧咧的道:“什么说书人,一只吠吠老狗!人和蛇的**之事乱弹一气,等我告上县衙,治你个伤风败俗的罪名!”
他一边愤愤着,一边暗自盘算如何出了这口气,不成想刚走进一个小胡同,两个青衣人围了上来,一左一右将他绑到了角落里,起手对着肚子就是一记重拳,然后不分手脚,全往身上招呼,并且这两人明显是有武艺在身,落点刁钻,痛彻入骨,外面还不见伤痕,真是下黑手的行家。
“记住,回家了闭上嘴!否则,钱塘湖里沉一家七口还是很容易的……”
“是是是,我知道,我闭嘴!你们别打了,放过我吧。”韩七心胆俱裂,跪地求饶,他家里一妻两妾,三个儿子,正好七口人。
钱塘城内的东市从晨时起就人头攒动,摩肩擦踵,一眼望不到尽头。作为区域贸易最为集中的场所,人流量向来是全县乃至周边数县之最,日间到这里来进行各类货物交易的人不下千余。
跟周七巧同样衣着装扮的人,站在市场最中的一处半人高的木台上,正以清晰明朗的口音讲着白蛇传。在他周围先是稀稀拉拉的十几人,然后变作数十人,再然后围了里外三层,后来的人需要拿着胡凳或砖石来垫脚才能看到台上的人,至于能不能听的清楚,就要看各自的耳力了。
“……那白素贞捏了剑诀,飞身入云,和蜈蚣精大战了起来,不下三百回合,突然隐了身,偷偷来到蜈蚣精身后,一剑刺向他的腰心。你想那宝剑何等锋利,立刻破开了黑甲没入了肌肤,喷出一股青色的血迹……”
“好!打的好!”周围响起震天的叫好声,观众的情绪完全被调动了起来,更有人高呼:“杀了他,杀了蜈蚣精!”这是入戏太深,已然快要成脑残粉的节奏了。
说书人看着台下,干咳一声,笑眯眯的道:“容我喝口水……”
轰!
又是一阵大笑,有识趣的马上喊道:“快快快,先生这是要润口之资,有钱的快捧个钱场……”
“那你这没钱的怎么办?”
这人嘿嘿一笑,不知从哪里寻来两根短短的圆木,举到高处啪啪一击,道:“我专门凑个人场!”
距离木台不远的地方聚拢着一群人,为的坐在胡床上,大冷的冬天穿着单薄的夹棉裲裆,两条胳膊赤条条的露在外面,要不是现在不流行纹身,估计会在肱二头肌纹上左青龙右白虎。
“那边乱糟糟的在干什么呢?”
“禀行主,好像是在说故事,我刚才去听了会,还他妈的挺有意思的。”
“故事?”
行主表示没兴趣,摸了摸肚子,眯着眼道:“你这惫懒狗儿,还有心去听故事,赶紧想想去哪给弟兄们弄点钱,三天没开张了……”
“嘿,行主可冤枉我了。”他凑到行主耳边,道:“你可知道那说故事的家伙是收钱的,叫什么润口资,我挤到前面瞧了瞧,怕是有上千文。”
“什么?说个破故事还能收钱?”
行主腾的坐了起来,怒道:“好啊,哪钻出来的羌奴,来我的地盘做买卖还不交厘金,胆子不小!”
羌奴是骂人的话,奴婢本就下等,加上胡人的羌字,更加的低人一等。至于厘金,也就是保护费,这些混迹在东市的游侠儿,聚众成党,收取商户的厘金,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了。
“走,去会会他!”
行主带着众人,手拿着棍棒,气势汹汹的刚走出数米,突然有一人冷冷道:“周相,到哪里去?”
行主一看,身子顿时软了,谄笑道:“市令,您怎么来了?”
一市的最高长官为市令,下属有市吏和录事,再下有蔷夫和门卒,负责治安管理等市务,在市场说一不二,权力极大。很多游侠儿组织跟市令或者市吏等都有来往,否则也不可能坦然处之的收取保护费吗,这点古今如一。
这个周相在东市的势力不算太大,跟市令攀不上交情,但跟市令身后站着的市吏交情颇深,每两三日都得聚一起吃吃喝喝嫖**,顺便将收来的保护费二一分作五,属于利益合作的狗肉朋友。
市令没搭理他,道:“来人,将这群持械乱市的贼子拿下!”
一群如狼似虎的蔷夫、门卒蜂拥而上,不等周相辩驳,就将他和一众手下制服于地,塞口缚手,无声息的押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