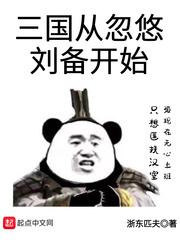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鸳鸯蝴蝶梦讲的是什么 > 183时髦的姐弟恋183(第1页)
183时髦的姐弟恋183(第1页)
庐隐的声名还是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个在政法大学读书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梦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会上他与庐隐邂逅,对庐隐寄予很深的同情,关心、体贴、劝慰庐隐,并向她表示爱意。
考虑自己的处境,庐隐有点自卑,觉得“我不应当爱他,也不配承受他的爱”。她抑制情感的依恋,理智地拒绝了他。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庐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语言讥讽她。卑鄙的是瞿竞带着一位靓丽的少女到庐隐面前炫耀,刺激她。庐隐被击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庐隐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灵上斑痕累累,她已把爱的梦想锁在心灵深处。苏雪林说“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对于这些人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他们开口求婚,庐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把他们轰出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
1928年,她认识了比她小9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
李唯建(1907年7月10日-1981年11月12日)系四川成都人。早年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过从较密,曾在《新月月刊》、《诗刊》、《贡献旬刊》、《人间世》等刊物发表新诗和译作。著有英文、散文诗集《生命之复活》,长诗《影》、《祈祷》,小品《唯建的漫谈》和《相思草》,以及译作《爱俪儿》、《英官外史》、《英国近代诗歌选译》、《四川军阀》等。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并于1978年应聘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英语教授。
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他们通信频繁,爱情急骤升温。李唯建的出现,如同阳光,照彻了庐隐的幽秘和阴暗。在化名“冷鸥”和“异云”的情书通信中,庐隐觉得她遇见了一个把她看透的人,那是李唯建给她的小诗:我握着你的心,我听你的心音。忽然轻忽然重.忽然热忽然冷。有时动有时静,我知道你最晰清。
面对着情感爆发的火山,庐隐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庐隐很不自信,问李唯建:“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年貌相当的女子,她比我好,对你更合适,怎么样?”李唯建的回答是:“难道恋爱能容得下第三个人?”庐隐开玩笑说:“我可是有名的扫帚星,你不怕?”“怕,我只怕取不到最近的距离欣赏你!
李唯建在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
庐隐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
关于恋爱,庐隐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是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
“一个有孩子的寡妇去和一个小自己9岁的年轻学生谈恋爱”的新闻迅速在校园内流传,庐隐开始被人调侃有着“小情人”。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劈天盖地而来。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庐隐可谓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量公开个人情书的女作家,在这部情书的结集中,庐隐如此坦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把戏也都尝试过了。从来没有一个了解我灵魂的人,现在我在无意中遇到你,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基于心灵的认识。异云,你想我是怎样欣幸?我常常为了你的了解而欢喜到流泪,真的,异云,我常常想上天使我认识你,一定是叫你来补偿我此前所受的坎坷。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庐隐陆续发表了小品文炼京小品》,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
被压迫的灵感,在这美丽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充满哀感,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李唯建回忆说:
我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我热烈地爱着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苦苦地探求着人生问题,并写信求教于泰戈尔,后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愿。1928年重返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庐隐,相谈投契。庐隐在城中教书,我住清华园。结识庐隐后,庐隐考虑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
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频繁的书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报》连载发表,庐隐自名“冷鸥”,名我为“异云”,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1933年夏天,夫妻二人有了一个小女孩名为李瀛仙,乳名“贝贝”。为了生活,二人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
其实庐隐拼命写作也是为了养家,“小爱人”李唯建一脑袋浪漫主义思想,有了女儿后就在家带孩子。庐隐劝他努力上进,他权当耳边风。这哥们儿也真是人才,在庐隐的散文《玫瑰的刺》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家庭小事:一天夜里,租住屋里出现盗贼的动静,庐隐建议李唯建去找同住的朋友帮忙,李在慌乱之中竟然打不开门“……为了建的缘故,我只得大着胆子走向门边帮他开门;其实那门很容易开,我微微用力一拧,便行了,不知建为什么总打不开。”
现在很多人都把庐隐与李唯建共处的四年奉为其最幸福的时光,而据张昌华先生考证“他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将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庐隐的朋友担心李唯建胡来,出面请舒新城介绍他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邵洵美在《庐隐的故事》里写道“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
虽然生活有压力,但庐隐情绪变得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这时期,庐隐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地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地反对旧势力,我大胆地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做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
庐隐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尖锐的斗争,不会不在她生活和思想里留下痕迹。她走向生活后,教过小学、中学,也当过一个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时代给她的社会经验是:中国的一切都濒于破产了。破毁了的社会当然还有希望,这是在最后她才认识了的。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摒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彻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地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
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一·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
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中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里说:“20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眷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拼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
可惜天妒红颜,1934年庐隐意外去世——为了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