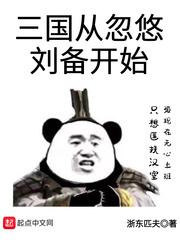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猫猫不吃东西没精神怎么回事 > 5 章(第2页)
5 章(第2页)
刚想完,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跟我说救助站那边申请好了,今天就可以把人送过去。
正好,还有时间,我打了个车,带着人到了城郊那个救助站。
一排老旧的房屋,看起来像二十世纪的建筑风格,白墙泛黄,贴地刷了半米高的绿漆,我有些不妙的感觉。
果然,进了里面,不太好闻的气味闷在空间里,一个房间里铺了半间的大通铺。
我知道像救助站这种非营利的公益机构,没有进项,只有出项,环境可能不会太好,但现实是,条件比我想象得还要差很多。
一旁的男人毫无所觉自己将要被丢在这儿,亦步亦趋地跟紧我,信任的眼神,让我忽然升起一股奇异的愧疚感。
虽然这样比喻救助站不太好,但就是有一种,将优雅的赛级纯白猫猫丢到煤矿场自生自灭的错觉。
我后悔了,当工作人员问起基本信息时,我问她可不可以不送过来。
她诧异地看我一眼,笑起来:「当然可以。」
她态度很好,可我很是愧疚,感觉给他们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连连表示抱歉,临走,还尽自己所能捐了一笔小钱。没法改善里面人的生活质量,但能让他们加一顿餐,也就足够了。
出了救助站,我向警方了解一下寻找家属的进度,对方回复我说快了,末了还奇怪地嘟囔一声,说好奇怪,这个人的亲属怎么比其他人难找。后面我都没听清,也就没放在心上。
收了手机,我看看面前努力缩进羽绒服帽子里的男人:「走吧,我们去甜品店。」
我知道一家老牌的甜品店,用料很实,现在是工作日上午,人估计也不多,很好逛,我们到的时候,许多甜品刚做好放出来,满店飘香。
正逛着,看到一个有点眼熟的人影,对方也发现了我,诧异又惊喜:「时婵,没想到能在A市遇到你。」
一男的,我父母家邻居的儿子。
12
我父母家在一个二线城市的小县城,他们还在高中年纪,就早恋搞大了肚子,辍学回家结婚,生下了我姐姐。
后来家里拆迁,意外得了一笔巨款,我父亲又染上了赌瘾,拆迁款很快就造完了,但是赌瘾没跟着完,接下来断断续续,赔了好多钱,家里一度穷得揭不开锅。
那个时候,我还很小,记忆里只有父亲又赌输了喝得烂醉,在那发脾气摔东西,偶尔还会对我母亲拳打脚踢。母亲不敢反抗,一直哭诉自己命苦。
可是有一次,我鼓起勇气拦在她面前,试图学着父亲凶狠的样子,替她挡了一棍子,费力捡起旁边的板凳想拿来自保,母亲却以为我要反击父亲,立马抢过板凳,扇我一巴掌,质问我为什么要对父亲不敬。
本来他们就更偏爱姐姐,对我这个多出来的一张吃饭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