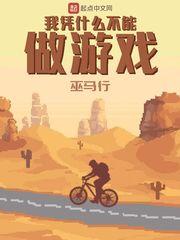笔下文学>专宠女尊 > 第150章(第1页)
第150章(第1页)
幼清正在给他做鞋样子,头也不抬,一针针扎得认真,“没使过什么法子,不高兴就不高兴嘛,谁还没个不高兴的时候。”
“也是,人都有个伤春悲秋的时候,熬过去就好了。”德昭挨她近些,低下头瞧她的绣工,兰草丛丛,黑底金线,极为细致齐整的功夫。
他伸出手触碰,手指尖刚挨着,便被幼清一巴掌轻轻推开,“别动,我绣着呢,仔细着绣歪了线。”
德昭怏怏地收回手,坐屋里屋里闷极了,幼清不同他说话,他守着她又不想出门,只得起身在屋里踱步,来回走了几圈。
小玉香炉鼎白烟腾,时光难逝,总得找些事情做。不一会,他抽纸研墨,一只手半撑着下巴,另一只手握笔作画,一笔一笔描着她绣花的模样。
半个时辰后,幼清做完手里的活计,抬眼才发现对面的人趴在短几上,眼睛阖着,手里犹握着笔,实际上早已梦游天际之外。
她瞧他压着的那张画,画的是她,画得倒也俏皮可爱。
她的目光自画上移开,德昭的睡颜近在眼前,这些天他着实累着了,每日天没亮便被召进宫,夜深时才得以回府。
她第一次用这样肆无忌惮的目光注视他。
当一个人从内心深处接受另一个人时,他便是她的少年了。
她伸手去擦他脸上不小心沾上的墨渍,指腹触及他的肌肤,冰冰凉凉,与他脾性不相称的细腻柔软。
大抵是爱人的触碰藏着火花,他这时忽地醒来,两人的目光撞在一起。
这距离让人脸红心跳。
德昭下意识撇开目光。
幼清往前俯了身子。
“王爷。”
“嗯?”
一瞬间,她的唇印上他的,这个吻几乎将他封印,他僵硬得连呼吸都忘了。
不知过了多久,久到他几乎瞥气窒息,幼清早已坐回原处,重新开始着手刺绣,他顶着一张憋红的脸,一动不动。
幼清瞄他一眼,声音又轻又柔,“王爷。”
德昭转过眼珠子瞧她。
“呼气。”
德昭慌忙低下脑袋,背过身大口呼吸。
幼清捏着细针,一针一脚地绣着,“你们男人真奇怪。”
德昭咽了咽,尚未回过神,“什么?”
她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眼神大胆地扫视他,“羞起来堪比豆蔻少女。”
德昭一愣。
“幼清。”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