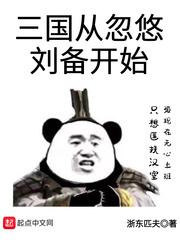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2、太子穿成本宫的猫 > 第31章(第1页)
第31章(第1页)
>
说完,苏良不敢再啰唆了,否则他不仅口才输给陆樽,甚至连小毛子都比不过。
一群人徒步进了景含隘,侍卫们先去寻找落脚处,留三、四个人保护陆樽等四人。
这里虽地处边疆,却不是真的有多破败落后,泥砖造的尖顶平房鳞次栉比,小商店林立,只不过与京城不同的是,街上很少人叫卖,路人也来往匆匆,甚少交谈,所以即使有人,还是安静得突兀。
“这里的气氛很奇怪啊……”陆樽狐疑地看着清冷的大街。
谷凝香却是美目一凝,语重心长地道:“看来这里许多人生了病是真的,我曾经到过感染瘟疫的地方,看起来就跟这里一样,人心惶惶,怕自己被病人传染,所以路上的人都对彼此敬而远之。就是不知道令他们害怕的病,究竟是不是如卷宗上所说的失魂症了。”
众人之间的气氛越发凝滞,不管这里盛行的是什么病,如果真会传染,他们几个外来人肯定首当其冲。
所以要离开?可是这景含隘看起来的确有古怪,说不定真是对付平南王的突破口,就这么离开如何甘心?
还拿不出一个主意,突然从街尾冲过来一个人,边跑还边大吼大叫着。
那人跑得近了,突然跌了一跤,接着就爬不起来,众人这才看清楚这是一个中年男子,全身伤痕累累,面目扭曲,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他口中毫无章法地喊着,“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有鬼啊,有鬼啊!”
谷凝香定定地看着那男子半晌,想走过去,手臂却被陆樽拉住。
“你放心,他这种情况绝对不是什么会传染的重症。”谷凝香以为他担心,认真地解释。
“我不是要阻止你,而是你不觉得,这种事应该由男人走在前面吗?你们女人跟在后面就好。”他勾起唇角不正经地笑了笑,径自朝那呈疯癫状的中年男子走过去。
谷凝香看着他的背影,目光中兴起一股笑意。
他……就连想保护她,都能把话说得那么混账吗?
到了那男人身前,陆樽确信他没有余力攻击别人,才让谷凝香微微靠近,而以陆樽站的位置来看,若是那人暴起,倒是能够第一时间压制他。
谷凝香对着那人看了半晌,也不嫌脏,伸手过去翻开了他的眼睑看了看,试着重按他几个穴道,接着试图和他说话。
但此人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是口中依旧喃喃自语着,“有鬼,有鬼啊……鬼要吃我了,鬼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我迟早会被鬼吃光的……”
她终于收回了手,拿出手巾擦拭,表情有些不自在地说道:“这不是失魂症,记得我上次说的奔豚症吗?他的情况与奔豚症相当类似。”
“上回?你可是比他漂亮多了,何苦拿他来比……”陆樽不由嘀咕着,让谷凝香的俏脸都热了起来。
她地白了他一眼后,才继续道:“奔豚症病者先觉腹部有剧痛,继而感到胃内有气体上冲,而痛处随之转移在喉部、胃部、或腹部。此症多是由于恐惧或惶恐不安造成,因为剧痛,病患易整天觉得自己快死去。
“而此人更是极端,长期处于恐惧之中,肝气郁结,劳倦伤脾,化邪内扰,损及心神,则神失所主,神离其位,只要一点小剌激,他便容易陷入幻觉,成了情志所伤的癔症。这并不是什么会传染的病症,不用担心。”
她的话才说完,这景含隘的百姓就像来反证她的话似的,一名大婶急匆匆地冲了过来,看到陆樽等人围着那中年男子,不由大叫着让他们退开。
“走开!走开,别碰他,小心被传染了疯病!”大婶的话语虽是好意,但怎么听怎么不友善。
谷凝香试着让她冷静,“这位大婶,这人不是疯了,而是癔症的一种,不会传染的。”
“明明就会啊!”大婶紧张地看着那中年男子,想扶他起来却又不敢。“咱们景含隘光是今年就出了十几个得疯病的,如果不是传染,怎么大家都得一样的病?”
大婶的话让谷凝香的脸色微微变了,看向众人的神情也变得十分凝重。
“如果许多人都得了一样的癔症,只怕他们是全都遭遇了同样令他们极度恐惧的事情,每个人的忍受度不同,才会前后发病。若真如此,那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了……”
陆樽等人协助将那中年男子带回他家中,他们见义勇为,不怕被传染的义行,立刻被景含隘当地的乡官知道了。
由于最近的外来人不多,他们一行人虽分头行事,但还是被猜出了是同一伙人,再加上还有一名显然医术精湛的大夫在场,所以乡官主动邀请他们至景含隘的会所中落脚,还特地宴请他们。
在宴席中,陆樽及谷凝香特地打探了这里病人的情况,果然听到那乡官愁眉苦脸地说,情况发生了约有半年,前些月每几天都有一个人会疯掉,一直到他们上个月请来法师做法,情况才好一些,但是疯掉的人没法痊愈,所以人心惶惶的气氛一直持续到现在。
他们还在乡官这里得到了一个关键的讯息,就是这些得了疯症者的症状,除了胡言乱语、神志不清、日渐消瘦之外,就是对外界强烈的畏惧,每个人都说撞鬼了,但没有人说得出鬼在哪里。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人半夜会梦游,跑出家门,接着人就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直到白天才会默默的自己回家。
久而久之,家人们也不再找了,反正横竖会自己回来,反倒是让整个镇上的人晚上都不敢出门,万一出门撞见一个,自个也染上疯病,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