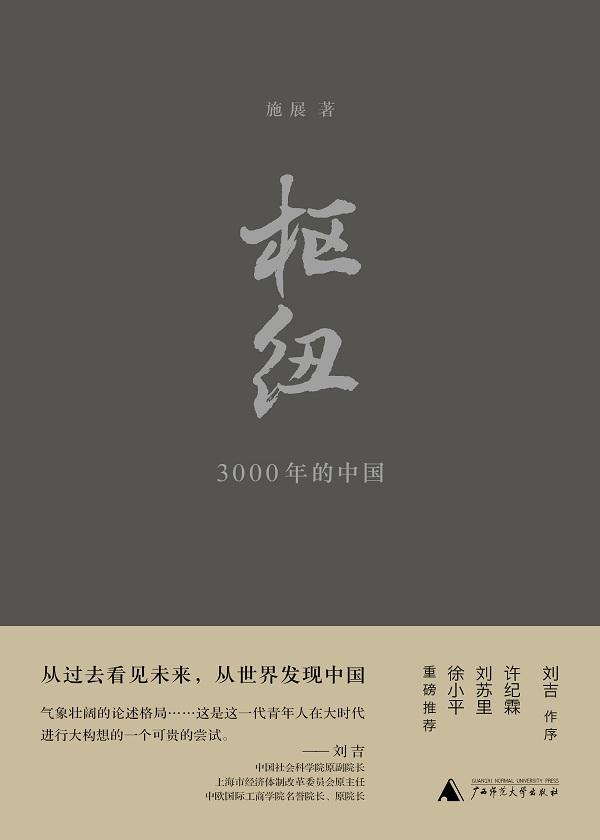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萌萌站起来林志玲原声 > 第122章(第1页)
第122章(第1页)
>
“所谓叛乱,只有初开始的几日闹得凶些,这几个月,平静异常,偶动兵戈也是点到为止,如您所见,现下街市照开,并无影响。”
这正是诡异的地方。嵇暮幽甚至一度怀疑赫兰反叛军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那边的土堡可是反叛军所在?”嵇暮幽掀起草帘一角,指了指中心城西边的土堡。
“正是。他们首领是一个叫崇修的,可没谁见过。”
嵇暮幽沉思,忽闻外面传来脚步声。
“军爷,可要再加点什么菜?”老板隔门问询。
“免了,吾还得去赶下一场呢,莫叫空等了。”嵇暮幽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在与老板错身时将一枚银锭搁在老板手心,“酒不错,下回还来。”
老板喜笑颜开,复拉着黑蜜一同躬身行礼。
嵇暮幽打算去土堡那边看看,如今中心城划分之处设了围栏,各自派人巡逻把守,正想着对策,忽然一人撞了过来,他一闪身,手已摁在刀柄,却看那人便滚倒在地,腾起一阵烟尘。
“我的爷,您好歹扶一把呢!”洛子兮吐净嘴里的土,牙齿上还沾着,遂抬手拿袖子揩干净。
嵇暮幽冷嗤一声,并未走近,此处人多耳杂,不便详谈。
“您撞了人竟无半点愧色吗?”洛子兮嚷叫起来,不远处巡守的士兵走过来,看是洛子兮,忙扶起来,“洛川,你如何这般狼狈!”
洛子兮立刻神色哀怨地喃喃:“算老子倒霉呗!”
话语飘入耳朵,嵇暮幽挑眉,毫不客气地在洛子兮胸口踹了一脚,将其踹出去三步远,看他半天爬不起身才满意地扬长而去,洛子兮蜷在地上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你无事吧。”几个守卫关切道。
“险些没给他踢死。”洛子兮捂着心口喘气,道:“那靖王是个目中无人的货色,我素与章仇将军不睦,他便低看我几分,如今我又彻底惹了他,怕是日后都没好日子过了,各位兄弟可要替我在余将军处多说些好话,趁早救了我去!”
“那是自然。洛兄弟的为人我们都知道,余将军上回听说,也想见见你呢。”
“真是多谢诸位弟兄了。”洛子兮虚拜一下,便给左右架起来去喝酒。
嵇暮幽行到无人处,从袖口中夹出洛子兮暗中递于其的纸条,上书:“三五之夜,必外出。”
最近的十五便在后日,嵇暮幽等得。
这日嵇暮幽从外厮混归来已是近晚,脚步踉跄,一看就是喝多了。余元开将其扶到帐中,端茶送水,好不殷切,直至帐中烛灭,方才退下。
不多时,余元开便换了常服出了营门。章仇阎此先看过轮值安排,今次看守营门的都是余元开的近卫,料定是刻意安排。故只有洛子兮,因和守卫一干混得熟,借口消遣三两句溜了出去。
洛子兮寻人不需跟着,他嗅觉灵敏,在孝敬余元开的头油里掺了香粉,仅凭着气味就能定下方位。最终在一处土堡停下脚步。
那土堡不偏不倚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地段,细窄如一根长针扎入土地,月色里静默地矗立着,隐约可见窗口有人影掠过,想来是把守的人。洛子兮恐贸然靠近惹人怀疑,绕至酒肆沽了两壶酒才折返回了营地。那些守卫笑他归来得忒早些,他苦恼似的蹙眉直道自己的相好今日不在,引得众人哄笑,借着话头顺便将两壶酒孝敬了。
隔日嵇暮幽同黑蜜说起洛子兮的发现,黑蜜咬紧嘴唇,道:“那是绿洲鬼市。”
嵇暮幽指节敲了敲桌子,示意黑蜜往下说。
“以前我们会在月圆之夜举办绿洲集-会,类似京中的庙会,自赫兰城破,便渐渐演变成了别的……即鬼市。”黑蜜面色发白,嘴唇不住哆嗦,“我去过那里……我是从那里被卖的……。”
嵇暮幽倒了杯热茶递给黑蜜,黑蜜顺势拢在手心,他闭目那一点温暖自掌心扩散,驱散周身恶寒,半晌终于又开口道:“那里如今是各种肮脏阴暗交易之所,人口贩卖甚至算是仁慈的了。”
“可知是谁在背后操纵?”
黑蜜摇头,他只是如羊一般被圈养贩卖,很难窥探到别的情报,“但我知道入内需要某种信物。”
猜到了,嵇暮幽略一沉吟,便有了主意。
晚间,营中马厩角落,十几个士兵聚众赌博,声音高亢,吵得马儿也睡不安生。
只见那名叫洛川的,跳到凳上,袖口挽至上臂,冲着牌桌歇斯底里地叫着“大大大!”看清骰子点数,登时一屁-股跌下来,将牌桌上的碎银一把推开,嚷道:“不玩了!不玩了!”
“别啊。”一圈士兵将其拉住,劝道:“愿赌服输,再者你早先也没少赢我们。”
洛川理亏,从腰间又搜摸出几点碎银拍在桌上,“就这些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怎么还恼了!”士兵中有十五那日守营门的哥们儿,他在余元开处得脸,大家都认他当大哥,“我们也不稀得这些,无非是凑在一起得趣。我是觉得你是个可交的,才同你一块儿玩。你要是甩脸子,便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夜里凉,马儿却被他们吵得缩在另一角,想暖和一下也不能,洛川吸吸鼻子,不无委屈地道:“实则不是玩得不尽兴,只是旁的不如意。”
那人立刻心领神会,“可是那章仇不给你好脸?”
“我是他家旧部,合该委以重任,他却对我极尽贬低,再说那靖王,非但不体恤,前几日还险些给我肋骨踢断。我本想到此处建功立业,光耀门楣,可眼下这光景,一是无战事,二则也不得重用,怕是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