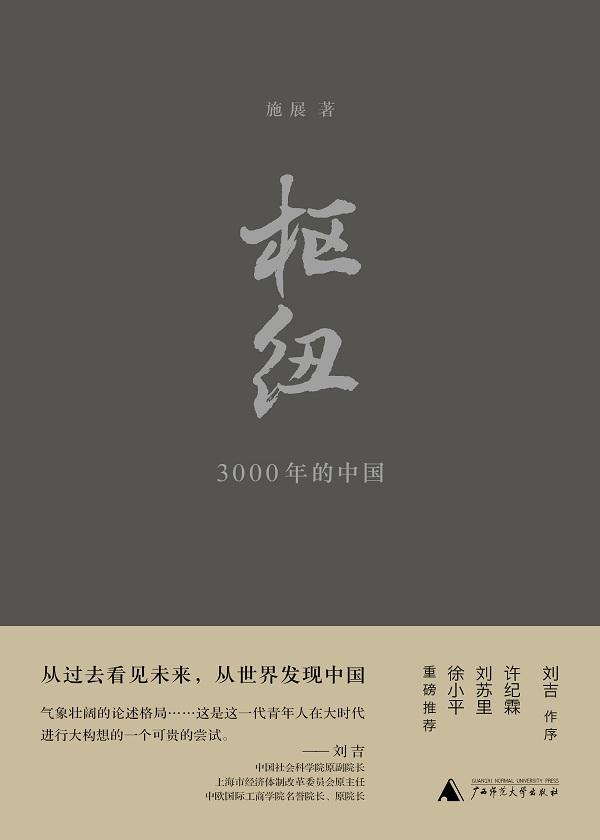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九龙城寨之围城的在线观看 > 第84章(第1页)
第84章(第1页)
>
别这么没出息了,只是淋淋雨,死不了的。阿暮心里想着。
眼看着最后一丝阳光躲进乌云里,这雨依然没有渐小的趋势,两人间的空气仿佛停止流动,阿暮的小腹不争气地又疼了起来,像被撕扯和拉拽。她蹙了蹙眉,终是打破了沉默:“你不是有话跟我说么?现在说吧,说完请你消失,别再跟踪我了。”
十几秒过去,预想的声音没有传来,阿暮疑惑着侧过头。王九仍保持着举伞的动作和体面的距离,他也远远看着前方,额前的头发已经被打湿,镜片上雨珠不断滴落。他眉眼间笼罩着几分疲惫,脸上难得地不带笑意,一本正经。
“……说完就要消失,我才不说。”他嘀咕道。
“你!”阿暮一时气堵,很快逼迫自己冷静下来,侧回身子不再理会。
随便吧,爱怎样怎样吧,反正淋雨感冒不舒服的那个不是自己。
只是刚才那一眼,怎么看见他的耳垂上好像多了个耳洞?一个大男人好端端地打什么耳洞。阿暮如果不是手里抱着东西,此刻真想给自己一耳光,为什么又开始想一些有的没的。
风吹得很冷,阿暮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怎么自己反而先着凉了?头顶的伞好像换了一只手支撑,一件还带着温度的大衣披在了自己身前,阻挡着冷风继续侵蚀。她忍住了没有说话,也没有偏头。两人还是保持着默契的沉默。
小腹一阵刺痛,阿暮不自觉地紧闭上眼,抿紧了嘴唇。
“你又受伤了?”低沉的男声染上了一丝焦急。
“我好得很,闭嘴。”疼痛让阿暮多了些不耐烦。都怪四仔,要是他晚传一小时消息自己也能把针施完,至少能止去一天的疼痛。
阿暮抱着油纸包的手不自觉用力,感觉额上有冷汗流下,大脑一阵眩晕过后她只觉双腿发软,几乎做好了晕倒在地的准备。只是可惜了这些药材,这要怎么好意思再问秋哥要一份啊。
阿暮差点急得叫出声,却只觉得身体一阵失重,下一秒睫毛几乎贴在熟悉的花衬衫上。
药材依然在怀里,抱着她的手臂依然支着伞,只是开车门的时候稍微费了点事。阿暮将后脑勺靠在座椅靠背上,沉重总算有了支撑,药包跌落在后座,但不碍事。她的左手捂上小腹,五指几乎在皮肤上抓出伤口,但可一缓内脏的疼痛。
“我送你去医院。”王九扶着她靠好后,转身准备去前排开车。阿暮赶紧用右手抓住他的手腕,反应过来后立刻松开了手,但还来不及收回就被一只温暖又粗粝的手掌紧紧握住。
“不用去医院,不是受伤。”阿暮用力挣扎了几下,那只手丝毫没有松动。
“你虚弱成这样,不是受伤是什么?”王九的语气难得的焦急。
“……是亲戚来了!”阿暮仰天,皱着眉解释。
“什么亲戚?”
“……大姨妈!”
“大姨妈是谁?”
阿暮觉得现在小腹已经不算疼了,更疼的是脑袋。失忆会把常识也失掉吗?这个人是怎么理直气壮地问出这个问题的?能不能直接开车去中学补一堂生物课啊!
还好,他并非没有常识,只是没理解这几个词的意思。阿暮大概花了一分钟就把事情解释清楚了,然后借着自己要施针的借口总算把右手收了回来。五分钟后,疼痛已散去不少,阿暮觉得总算能清醒地坚持到回城寨了。她收回针,又抹去了额头的汗水。
王九全程安静地坐在后座一旁,没有说话,只是担忧地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他身前确实被雨淋湿了不少,耳朵上也确多出了两个耳洞,甚至仍泛着红。阿暮告诉自己不要问,她不关心。
将药材重新捡起抱在怀里,阿暮准备从左侧车门直接出去,外面的雨已经停了。秋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突然。
身子刚刚向左偏过,就被人从背后抱了个满怀。王九双臂紧紧环着她的腰身,脸埋在颈窝,力气大到她无法动弹,就像害怕她像这雨雾一般忽然消散。
刚收好的药包又掉落在地,可阿暮来不及生气,她的情绪被不舍和理智撕扯成两半,终是理智占了上风。
“松手。”阿暮声音冰冷,身后的人闻丝不动,炽热的气息吹向她的颈间,拂过她尚清醒的心。
手臂被箍得很紧,没有抽离的可能。但手腕还算自由,她从袖袋里抽出三根全新的银针,毫不犹豫地对着王九的手臂扎了下去。他的手臂肉眼可见地颤动了一下,阿暮立刻闭上了眼睛。
“再说一遍,松手。”阿暮扎的是痛觉最敏感的几个穴道,可身上这份力气还是没有丝毫松懈。
她宁愿他们刀剑相向,也好过现下哀毁骨立。
她假装心脏不再跳动,握着针的力度又向下推进几分,她清楚,足够痛自然就会放手了,那就痛到满意为止。
耳畔传来一声沉闷的低吼,那是痛楚从喉间溢出的具象。周身的力气有一须臾的松动,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力道,好像要把她揽进身体里。
这次颤抖的是她的手。
没出息!阿暮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呼吸声都发着抖,她手指猛一收力,把银针全数撤回,因疼痛而布满青筋的手臂上渗出了三个血点。那血点小如蚂蚁,世人皆不可见,痛苦却可啃噬其骨。
阿暮觉得心脏被揪成一团,骨头也泛着疼,可这些只能让自己知道。她努力学着,把心慌意乱伪装成不以为意。
“我身上什么也没有。”阿暮小声低语,声音难以置信的冷静。她垂着眸,把周边的环境幻视成果栏那一夜,把所有的心绪也拉回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