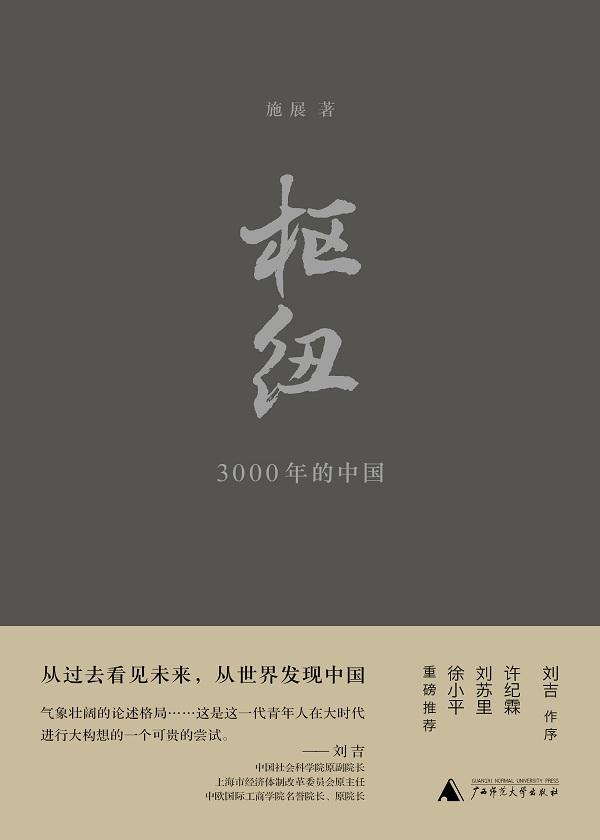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精分大佬她在线装究 > 第七章(第1页)
第七章(第1页)
肖魇夜打小就在三教九流的地方长大的,在那样混乱不堪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的熏陶下,早早就学会了听弦外之音的本事,所以林白的欲意,肖魇夜再明白不过。
想跟他保持距离,甚至敬而远之的人比比皆是。谁也不闲自己命长,活的太自在得意,想找点刺激,死的快点。跟他这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只要沾点边儿,别说警方请你喝茶聊天,就是小命也说不好会成为谁的目标。
这些肖魇夜心里都再清楚不过,甚至可以算得上是难得深明大义的理解。可唯独面前这个女人,她刻意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态度,叫他莫名的烦躁气氛。
“女人,我耐心不多。”这才和这女人说了没几句话,肖魇夜已经感觉自己被气的体力不支,脸上的好不容养出来那点血色,也迅速退成了一片惨白。
“刚好肖先生,我时间也不多。算是来跟你道个别,明天我就会离开这里。”
想走?
肖魇夜轻挑一侧如剑锋的眉毛,“我还没痊愈,女人,你哪里都去不了。”凛冽的声音如同寒风中松针,刺在人身上又痛又痒,让人咬牙切齿的同时又没有选择的权利。
林白脑子里搜索着从修炼那里得来,针对于自己目前处境的形容词,好像叫做“非法禁锢”。
“肖先生,没人跟你说,非法禁锢是违法的吗?”
肖魇夜:“女人,你跟我讲法律?”
等同于必死之人跟医生说“我能抢救一下。”是一样的道理,听起来像个笑话。
从肖魇夜轻蔑的眼神中,林白觉得自己脑子瓦特掉了,跟不要命的人讲法律,并不是个明智之举。
林白向来不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她接受自己的错误,并且善于总结,于是她换了一种方式,说:“肖先生,你身上的伤很显然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以你强壮的体魄,相信会比常人恢复的更快,实在不需要我留下来。”林白又想了想,可能觉得自己的理由还不够充分,于是又说道:“更何况,我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回去处理。”
是很重要的工作,等着她回去开膛破肚的尸体,已经可以绕地球一圈。
然而肖魇夜的态度似乎铁了心的不让她离开,“女人。你觉得你现在有跟我讲条件的资格吗?”
林白:“…”
缺乏人气儿、不善于与人沟通的的林白,一向都是她叫人如梗在喉的堵的上不来气,如今第一次被别人堵的说不上话倒是第一次。
肖魇夜冷哼一声,对于林白怔松的表情十分满意。认为林白终究是个女人,孤身在他们这群穷凶极恶的男人堆里,感到害怕才是正常反应。
林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甚至连心跳过速的时候都很少,这还要多亏了她那人不人,鬼不鬼的工作成就了她对生死淡薄的观念。
林白具有双重身份,其一是医学院士,脑外科权威医师,主治活人。其二是司法部门外援法医,主治死人。从手术台上下来,转身进验尸间,是林白常有的工作状态。时间长了,对生死都淡泊了,自然对外界刺激什么的变得迟钝起来。所以肖魇夜的一点窃喜是注定要落空的。
自鸣得意的肖魇夜,带着挑衅的眼神看着一动不动的林白,浅薄的嘴唇已经控制不住想要上扬起胜利的姿势,“女人,就应该乖乖听话,弱势群体的动物,寻求强者的庇佑才是明智之举。”
林白实在忍无可忍的翻了个白眼,觉得自己面前可能是一头食古不化的蠢驴,在现代社会里耍着封建古代男尊女卑的流氓。偏激的思想叫人感到恶心。叫林白恨不得送他点自己发明的小东西,当作是替天行道。
“男人”情绪已彻底转为不快,林白清凛的嗓音,在这不变黑白的房间里显得十分空洞幽灵,“你的命是女人给你捡回来的,想要骨气?现在就可以去死了。”
“你敢叫我去死?”肖魇夜从未被女人如此叫嚣过,气急的想要起身下床,却在身上传来撕裂的疼痛之下,不甘心的收住了动作。
“怎么怕死?”林白从座位上起身,缓缓走至肖魇夜床边,居高临下的眼神中带着轻蔑,半眯着的眼睛,将床上的男人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然后鄙夷嫌弃的继续说道:“还是怕疼?”
一口牙几乎快咬碎,肖魇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把将林白带进床上,布满红血丝的双眼,如同被激怒的野兽般盯着坐在自己腿上的林白。
“女人,如果你想激怒我。那么你成功了。”
原本以为应该惊恐的脸上,此刻却风平浪静,平静的连一丝涟漪都瞧不见。林白将双眸拉长,微眯起来像是在笑,又或者在鄙夷着。一根白皙修长的手指如同毒蛇的信子,冰冷且诱惑的在肖魇夜的胸口游移。
“肖先生,你忘记了?我是你的主治医生……”
话音落下,林白在他左肩上稍一用力,红色便如同染料一般,将白色的纱布晕染开来。林白了解他身上的每一处伤口所在,老人常说,宁得罪小人,莫得罪女人。尤其是学医的女人。
本该疼的龇牙咧嘴的男人,竟连一丝动静都没发出来,林白又加重了些力道。可惜除了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林白并未得到自己预期中的反应,可惜的在心里咂了一声,心想“这个男人倒是挺有毅力的。”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我除了是名医生,还是名法医?”
修炼曾告诉过自己,语言是良药,亦是凶手。林白见暴力不能解决,便转换了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