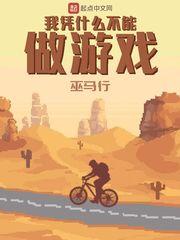笔下文学>正邪不两立txt清静 > 第3章(第2页)
第3章(第2页)
“你是今天新来的转校生?”
谢鄂抬头,一个身形高大魁梧,完全符合他想象中杨基地下老大的光头男孩带着五六个同伴挡在他前面。校服松垮地套着,下摆露出一截白衬衫也不知沾了什么,色彩诡异。眉毛很浓,斜眼睨着自己。
再看看周围,好象是个巷子,不大也不深,可是看到这架式,本来要进巷子的人都转身退出去。
“你就是郑直同学?”谢鄂试探地问。
光头与其他几人对看了眼,眉毛皱得更深:“大爷手上不便,缺了点钱,你识相地就好好孝敬大爷,这样才能在杨基呆下去。”
“果然是勒索。”谢鄂叹气:“这么明目张胆,不怕进局子?”
“嘿,要论关系,哪个派部的不称我们老大一声大少,谁敢对他动手。”旁边的小弟得意洋洋,往前迈了两三步,顺脚踢开路边一块挡道的石头。石头骨碌碌滚开两三米,撞倒了不知是谁搁在路边的纸箱,纸箱一侧,纸箱上的竹竿掉了下来,乒乒乓乓一连串声响,动静大得巷头巷尾都有人探头看过来。
要不要趁乱跑走?跑到大街上去喊救命?谢鄂有些苦恼地思考。
“你这笨蛋,搞什么鬼!”同样被动静吓到的光头摔了同伴一记响头。
“老……老大。”光头身后染着红发的小弟惊叫了声:“你看……”
掉开的竹竿后面还有箱子,箱子上坐了个男孩,正懒洋洋地看着大家。
城市里的光线并不好,夕阳照进小巷,光波在空气中折过几折,只剩黯淡的残影。谢鄂转向黑暗而急剧收缩的瞳孔中,只看到男孩头发颜色非常地黑,纯粹的鸦色。
他后来才想到,那是因为男孩皮肤特别白,才衬得头发特别黑,左耳上挂着个鲜红的流苏坠子。黑、红、白三色都是极为纯粹的色彩,一时间,除了这三种颜色外,再没有其他印象。
“是……是你!”光头口吃。
“是我。”男孩摇了摇头:“真是不幸。”
“我们走!”光头被针扎到一样马上转身跑走,理也不理呆在一旁的谢鄂。
这男孩是谁?居然能让杨基地下老大一句废话都不敢多说就跑了?谢鄂张大嘴。
男孩转头打量他:“他刚才在勒索你?”
“呃,是的。”
“我救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