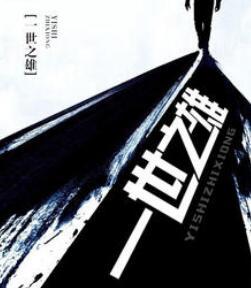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棺椁摇梦铃第4章 > 第50章(第1页)
第50章(第1页)
>
邢正不想听他打岔,敲了敲书桌,“你也识字,自己来看!”
“嘿!瞧把你神气的!”
裴元长袖一挥,一般摇着折扇一边气冲冲朝邢正大步而去,抄起桌上的宣纸便快速地看了起来。
“混账!”他一目十行,很快就读完了。
“我现在就让人把石芸娘给抓起来。”
三枚摇头:“石芸娘,离了这老妪,难成大器。”
接过八耳嘴里的油纸伞,将线绳的另一端绕着伞骨上的红点缠好,三枚接着才道:“油纸伞就是一个隐藏的关键。”
“薛婉茹刚出生时,薛父和石芸娘便为她做了一把天青色的油纸伞,甚至还在伞骨做了独特的徽记。不管是左邻右舍还是亲朋好友都知她下雨天,惯爱撑着那把伞,所以并未提及这个信息,是很合逻辑,甚至是父母关爱子女的细心体现。”
邢正想了想,确实除了薛婉茹他们一家,其他人家都是含糊带了伞出门,并不记得伞面确切的颜色或者样式。
三枚:“但有了这么一个线索,到时候你们官府的人,若是找到了一把昏黄色的油纸伞,那便意味着薛婉茹死了,若是没有,石芸娘她们便得小心提防,难保哪天薛婉茹就杀了过来。”
陆衎:“但当初安然从雨林找到的油纸伞,却是天青色的,和老妪自我封印进去的油纸伞,怎么看怎么像是同一把伞。”
三枚却摇头:“不一样。”
“你们若是仔细对比看看的话,便能发现,伞骨徽记上的朱红点迹,颜色深浅并不一样。”
薛父制伞的习惯,除了习惯刻上徽记,还喜欢制作一把备用,而那把备用的,用的是家里保存的竹料,所以伞骨上没有被老妪偷摸点上自己的心头血。
“雨林里的油纸伞,是薛婉茹从家带出来的那把,但是发生冲突的时候,不知道丢在了哪里找不到了。而老妪的这把,是石芸娘家里备用的那把,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放在云客来的。”
“当啷!”
放在桌上的破瓷碗,突然响起了一声铃声。
绑在昏黄色油纸伞上的线绳,慢慢地立了起来,接着顺时针转起了圈,沉在破碗水底的线绳,被一点一点地抽了出去,紧紧地缠在伞骨上。
桌上的碗随着线绳的拉扯,一点一点地移到桌沿,就在裴元忍不住要伸手护着的时候,雨伞绕圈的动作停住了。
外头劈啪作响的雨声好似渐渐消停了下来,呼啸的风声不再咆叫个不停。
“雨变小了,要停了吗?”
裴元抬眸看向自己小心挂在窗户口的稻草人,“咦,你们快看,那稻草人好像活了起来,正拿着扫帚扫着雨水呢!”
众人闻声看去,果然就见粗糙得十分抽象的稻草人,动作一卡一顿地左右扫着什么东西。
八耳仰天“咯!”了一声,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后,鸡头45°朝天仰,昂头挺胸逗猫遛狗似的,一踢一顿,一踢一顿,将封印着老妪的那把油纸伞,踢到了线绳的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