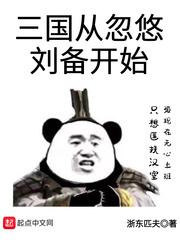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升斗小民猜生肖 > 第193章(第1页)
第193章(第1页)
>
“好端端的你不在玕州待着,怎么跑到秀州来了?”秦黍虽这般问,但总算额图浑是个知事儿的,过来之前先给她捎了一封信函过来了,所以人真来了秦黍倒也没那般措手不及。
额图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憨憨地笑了一声,秦黍一看倒是吓得不轻,她忙摆手,“额图浑,你拿这副面孔对着我,我倒是要好好想想你这次过来谈的买卖有多大了。”
秦黍犹记得第一次同额图浑见面时的场景,她深知额图浑是个面憨心黑的主儿。虽说两人在前头两次的来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但她还是架不住额图浑朝她憨笑一声,他一笑,秦黍心肝就是一颤,下意识就想去摸自己荷包里头的银子。
这人看着就像来骗她兜里钱来的!
秦黍忙拿起茶杯自己饮了一口茶,压压惊。她和额图浑相对而坐,最终还是没忍住先问道:“额图浑,你们部落人谈事儿向来爽快。你这次过来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儿?”
额图浑见把人吓着了,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只是没摸到部落人的小辫儿,而是摸到包裹整齐的发髻,他手顿了一下,他忘了这次过来是乔装成大燕人的样子了。
“我们首领想跟你合作。”
“合作?”秦黍放下茶杯,看向额图浑,“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合作。”
额图浑笑了一声,看着秦黍那双分外诚挚的眼,知道她并没有说虚话在哄骗他。
额图浑垂眸,看着手中白如霜雪的瓷杯,嘴里却说起与此不相关的话题,“都道大燕的玉瓷难得,蓟州的互市上就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瓷杯。”
秦黍哑然。
黑水部虽在白山黑水之间,但日子也不是那般好过的。先不说那酷寒的气候,单只是胡虏在一旁的窥伺就叫他们起居难卧了。胡虏的骑兵一向厉害,他们秋猎南下的时候在大燕讨不到便宜,就会转而向东闻黑水部讨要,所以哪怕黑水部有山利之便但也架不住胡虏东下讨要一次,这也是黑水部山中珍奇无数,但部落仍旧不富裕的原因。
这样一来蓟州的互市上,黑水部的盈余便只能用来换取所需要的口粮布匹了。至于瓷器这等享乐之物不说互市上出现的少,就算偶有几件出来,黑水部也少有人会去拿那珍贵的物资去换这类东西,是以这大燕的玉瓷在黑水部珍稀得紧,在黑水部的声名也远比在大燕更如雷贯耳。
秦黍看了一眼额图浑,心里头已经转过几个念头,她用指尖无声地轻敲了几下桌面,就着莹莹烛火拢着的光亮看向对面的额图浑,“……所以你们黑水部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了?”
闻言,额图浑笑了一声,笑声有些凉,“我记得你们大燕有个词是叫什么来着,”说着他拍了下自己的头,而后恍然想起,脱口道:“对,就是‘朝不保夕’!”
“黑水部依水而生,又秉承山神恩泽,我们是山神的子民,不是北边那群被抛弃了的豺狼。”所以他们黑水部落的日子理当是富足安乐的。
可是在胡虏铁蹄下,他们黑水部忘记了山神的遗泽,成为胡虏的彘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在蓟州的边境茍延残喘着。
这不是黑水部想要的生活,这也不是黑水部落的宿命。
和秦黍的两次生意往来,让黑水部看到了挣脱脖子上那道无形锁链的曙光。
昏浊的灯火中,这个黑水部的汉子如是道:“我们部落从来不是为了打仗而生,如果能不费一刀一剑便能过上饱腹的日子,部落人愿意放下手中的戈矛长枪。”
秦黍迎着额图浑的视线回望过去,她定定地看了他几秒,不得不赞一句黑水部首领的眼光,他很会知人善用。额图浑是一个很厉害的生意人。生意场上的情和利都让他玩明白了。
他拿着黑水部首领的命令来与秦黍谈合作,合作便是生意场上的事儿,那自然就是钉是钉铆是铆一开始就要事事讲清楚,但额图浑一上来先拿黑水部落的悲惨历史来说事儿,这打的便是感情牌了。
可偏偏秦黍还就吃这套,这倒不是秦黍心慈手软,而是额图浑的话是实打实地将黑水部面临的困境摆到秦黍的面前,黑水部的困境便是黑水部的弱点,而额图浑的真诚便是将黑水部的弱点摆到秦黍的面前,秦黍便知道,这是黑水部此次合作的诚意了。
但该问的还是要问,“你们为什么会找上我?”
玕州商贸发达,各类的商人都有。额图浑在玕州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那些商人的内里乾坤。做生意嘛,理当选个实力强的背后有靠山的不是。
想到这里,秦黍突然知道黑水部选择自己的原因了。
果然,额图浑的回答便是,“那次齐宁河道淤堵,但偏偏你的粮船安然无恙地过来了。”
齐宁河那趟运粮之于秦黍来说属实凶险,但凡是陈家商号大管事脑子稍微慢点,亦或者春伯脑子糊涂点,黑水部的那批粮可就算是断送在了齐宁河上了。
秦黍是知道运粮内情的,是以她没觉得那次运粮成功是实力的原因,她觉得那次纯粹是老天爷给面子,天时人和都让她占到了。
然而黑水部却不若秦黍这般想。在他们看来,在齐宁河河道淤塞的情况下,秦黍的运粮船不仅能准时到达蓟州且粮食分粒不少,一能看出秦黍不凡的实力来二还能看出秦黍在官道上深厚的依仗来。毕竟蓟玕一线,沿路那些官如同匪一般不好打发。能将这些人轻易打发了,那只能说明在官道儿上,秦黍背后的依仗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厉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