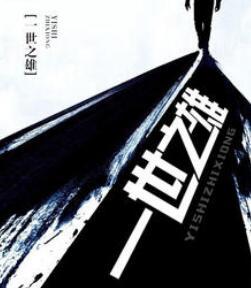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养歪偏执皇子死遁后半纸千山 > 第69章(第2页)
第69章(第2页)
本想自己偷偷溜进房间上点药,裹裹伤,还被楚凤歌逮个正着。
他叹了口气,安慰楚凤歌道:“没多大事,看着吓人,其实就是破了点皮。”
楚凤歌看起来比他还疼似的,道:“哪有这么简单!伤口在马鞍上生生磨了一路!”
他把手伸到苏遐州鼻子最底下,生气道;“你自己看!都渗过亵裤,一摸一手都是血!”
唉你……说的人觉得更疼了。
楚凤歌坚定道:“我抱先生去房间!上药!”
说着半蹲下身,看起来下一刻就要抄过苏遐州的膝弯,真的当着驿站所有人面把他抱上楼了。
苏遐州及时道:“等等!殿下!六郎!我自己走!”
楚凤歌沉默地盯了他片刻,道:“我扶你。”
他这一句说得不容置疑,苏遐州自己也确实挪不下去了,只好点点头,任由楚凤歌抄着他的膀子,架着他进了驿站。
就算只是这样,驿站里歇脚的军官、忙活的驿卒也都或是偷眼、或是直接盯着他们看上了。
楚凤歌皱着眉,喝道:“看什么看?!”
一副霸王样子。
在场的哪个不知道他是景和帝宠爱的幼子、开罪不起?
可偏偏这一队人中,只有苏遐州的身份讳莫如深,没人知道他是哪来的,为什么会跟着他们执行如此秘密的军令。
再加上眼见着楚凤歌跟他亲密异常……
连房间,楚王都特意吩咐要和他分在一间……
当即虽说个个扭开头,假装闲聊,却在他们转过身的时候,八卦得更起劲了。
苏遐州被看得如芒在背,榨出最后一点体力,飞也似的奋力爬上二楼去了。
直到楼梯隔绝了这些探究的视线,苏遐州才松了口气。
楚凤歌几乎是把他架起来,双脚离地,道:“快去上药!”
半推半就挪到了房间,苏遐州几乎是一摸到床边,人就瘫了。
驿站中来来往往都是策马的达官显贵、加急信使,因此常备金疮药。
楚凤歌翻了药出来,走到床边,道:“先生,裤子脱了。”
“……”苏遐州都没劲儿惊恐了,他有气无力道:“劳烦六郎出去片刻,我自己上药就行了。”
楚凤歌却道:“你伤在后面,自己看不见,如何上药?”
苏遐州语塞。
双手却忠实地体现了他的态度——他牢牢抓住了自己裤腰,说什么也不肯松手。
说实话,他现在一和楚凤歌靠得太近就浑身别扭,更别说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坦诚相见了。
虽然楚凤歌好像根本一点都没往那方面想……
好在楚凤歌没有再质问他是不是还没有原谅他之前用强的事。
他沉默地看了苏遐州一阵子,妥协道:“我把眼睛蒙起来,不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