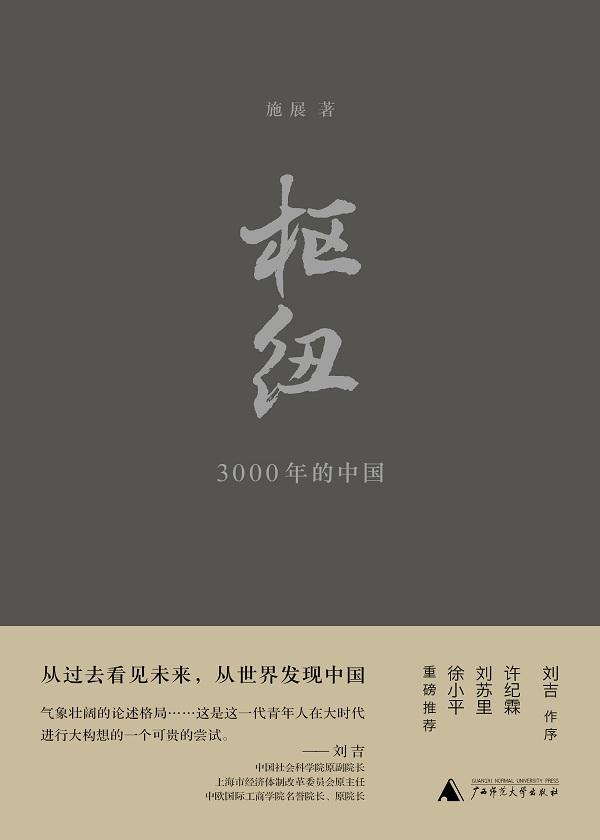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浮梦旧笔全本免费 > 第23章(第2页)
第23章(第2页)
“时追多谢郎君。”
雷刹道:“我不过身入迷障之中,你非真,连我己身都是虚像。”他立刀泥中,手过利刃,摊开掌,掌中血淋淋的伤口转瞬即癒。
“既如此,郎君不如当作一梦。饮梦中酒,听梦中事。”风寄娘与老叔一坐一立侯在堂中,连枝灯盏红烛泪垂,食案备着几碟小菜,一壶清酒。
雷刹在一方坐下,有菜便吃有酒便饮,静看他们耍得什么鬼把戏。
时追将银铃系在颈间,行动间银铃声响,他在案前坐下,重施一礼:“时追见过雷副帅。”
雷刹道:“你们装神弄鬼唱这出戏,定有话说。”
时追认罪道:“命当以命还,如夫人杀了老夫人,我杀了如夫人,我可有错?”
他问:“我有罪?可我有错?如夫人不该杀吗?”
“时追,你过界了,你可悔?”风寄娘轻声叹道。
时追歪了歪头:“悔?那是什么?我生于人间,却不懂人间事。”他执盏敬雷刹一杯酒,“劳副帅将真相示于众人跟前,我有罪,她虽身死,并不无辜。”
雷刹道:“届时,我去何处寻你这个凶手?”
“不敢失信副帅,寄娘作保。”时追正色道。
雷刹略抬了抬眉:“她?她在我心中轻浮随性,不足为信。”
时追皱眉,无措道:“我身无长物,我所有的皆老夫人所赠。”
“那便把银铃留下。”雷刹道。
时追满目不舍,迟疑片刻咬牙点头,取下银铃重又交回雷刹手里。
雷刹又叫老叔送上纸笔,写好罪状让时追画押,时追眨眨眼,拿起来好奇地看了看,咬破手指在上面印一个血指印,许是怕了雷刹嫌他不够诚心,印了一个不算,又连印了好几个。
“够了。”雷刹看状纸被血指印印得血糊一片,有心再写一张让时追重印,想想又作罢。
风寄娘举壶斟满酒杯,玉手轻执奉于雷刹:“郎君慢饮这杯‘故人归’。”
雷刹疑她在酒中作怪,也不推辞,接过饮尽,酒入喉间清冽甘美,琼浆玉液不过如此,盯着风寄娘道:“今日之事,雷某记下。”
这酒味甜,酒劲却十足,雷刹一杯入肚,头沉目重,往案上一趴,醉了过去。等再醒来,天已大明,荒寺陋园,阶前院中十数株枯枝牡丹,黄雀在枝头叽喳吵闹,蚊蝇振翅嗡嗡飞过。
雷刹只感头疼欲裂,看四周风寄娘与老叔不见踪影,案上也无残羹空杯。惊身坐起,摸摸怀中,摸出一对银铃和一张四方叠起的罪状,展开一看,正是自己笔迹,再看具名……几个暗色的猫爪印。
雷刹盯着罪状半晌,这才绷着脸重将它叠好收进怀中,在寺中转了几圈,虽然野草肆虐,却有烟火之气,一时怎也寻不到风寄娘与老叔,通往前殿的过道,荒草枯树拦路,无处下脚,只得循着昨日来路出了后山小门拾阶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