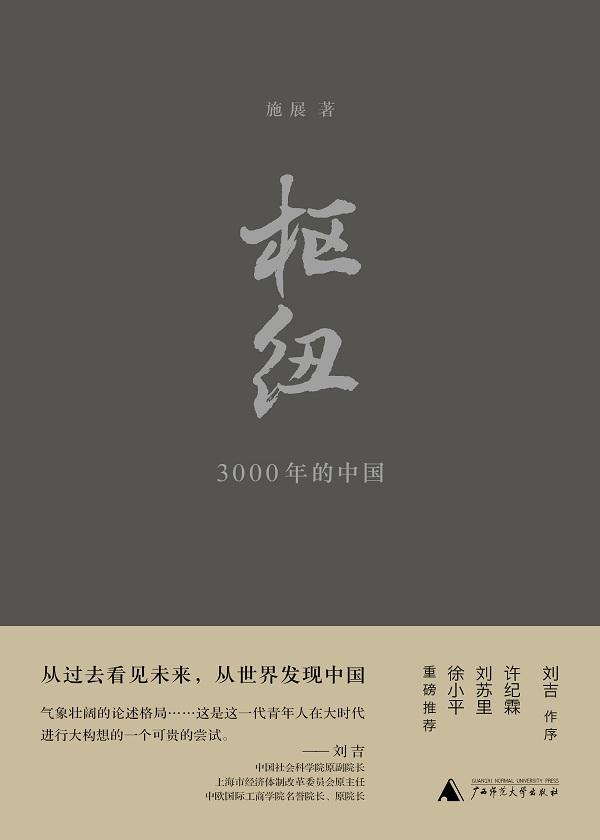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海神曰海若 > 4 章(第2页)
4 章(第2页)
而聂虚尚为幼子时,村长去他家走动得最勤快,名义上是监督他大伯一家待好他,可实际上呢?
头几年村长还护着他,后面突然有一天开始就不来了。
导致大伯一家行事逐渐偏颇。
所以,村长为何突然转了性呢?
这些碎语,我也是在闲聊的村民嘴里听得的。
「拿出来,物归原主,不然我可就喊人了。」我下巴点了点一桌子的肉,以示威胁。
村长像老了十岁,顷刻间,整个人颓废了下去,他哆哆嗦嗦地从地上爬起,摸上倒在一旁的拐杖,颤悠悠地从一旁的冷灶里摸出一个盒子来。
我看得满头大汗,这老东西也不怕被烧了!
「放心吧,烧不坏。」村长肉疼地咬着牙狠狠说道。
真是妙啊!这东西烧不坏,所以他才随意丢进灶里,有宵小进来,哪会想到起火的灶里也藏东西了!
我接过去捣鼓了下,打不开,只得收了起来。
「聂虚大伯……你做的?」我拿起筷子挑了块黏稠发冷的肉出来,除了腥臭还带着一股子酸味。
村长捏紧了拐杖,脚步虚浮,额角冷汗簌簌:「不是我!」
这模样,不是他是谁?
这老头子在村里威信高,随意寻个借口就可以将聂虚大伯骗来,村里男人都好酒,一包迷药下去,神魂不知。
我也不管他如何狡辩,千不该万不该把罪名安聂虚头上,连累我受了罪。
想到聂虚漂亮的脸上那两道刚结痂的血痕,离开的时候我特意在院子里的干柴堆上扔了把火,然后掐着嗓音在角落里嚎了一嗓子:「着火啦!」
屋内「哐啷当」,夹含咒骂声。
回到破庙时,恰巧碰到聂虚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他像提溜只兔子一样拽起我就跑。
我俩净挑幽暗无人的小路走,倒也奇怪,我只在村长家放了火,为何沿路走来,着火的不止村长一家?
站在村口往回眺望时,我扯了扯聂虚的衣袖:「你干的?」
聂虚红着脸,怯怯地盯着我,从胸口掏出一把鲛珠来。
嚯!这些不是被抢走的那些鲛珠吗?
我目瞪口呆。
合着你不是回去看你侄子去了?
「给、给……给阿若。抢、抢不……不走。」他放到我手心里,掌心滚烫,像灼烧的炙石,烫得我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