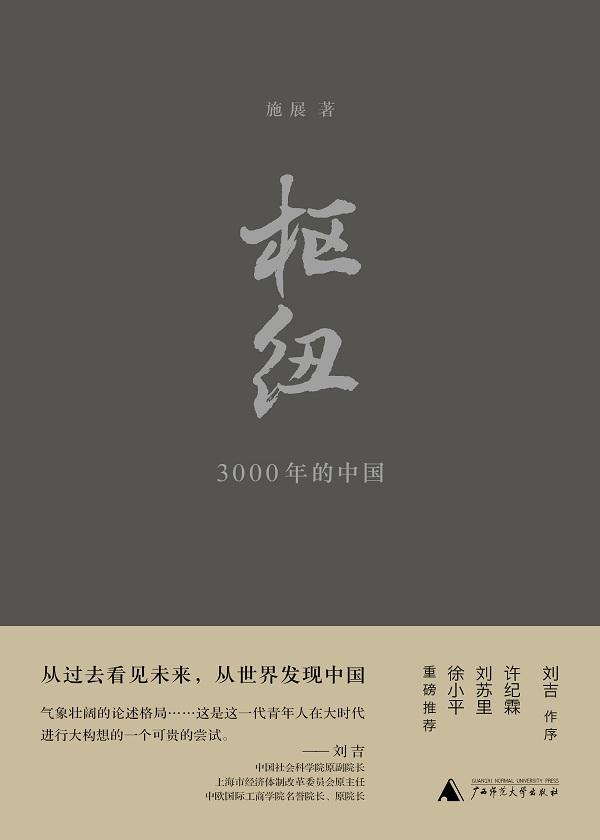笔下文学>多情却被无情恼全诗古诗词名句 > 6 章(第1页)
6 章(第1页)
饶过我们了。」
「秋宫人说的当真?」绿蕙简直难以置信,握住了她的手,仍是止不住哆嗦,「我还有命在,我年底还能放出宫吗?」
「能!」秋水点一点头,他是君王,答应了的事,一言九鼎,绝不反悔的。
一时间,绿蕙和赤瑕从大悲到大喜,都惊得不知如何是好,抱着头在一处呜咽。
陈宝林亦擦了擦眼角,半晌,牵住了秋水的衣袖:「姐姐别怕,往后总还有我陪着姐姐。」
秋水失笑,长留宫中有什么可怕的,便是做皇后时,也不是说离宫就离宫的。
只是,他能这么轻易就应了她的哀求,倒有些让人出乎意料。
上旬月侍寝的妃子原就不多,且都顾及着身份,不争那一天两天的工夫,是以平日里几大上位宫妃表面上倒也处得甚是和睦。
孰料,半路杀出个陈宝林,居然也在上旬月接了驾,众妃这下子都有些不甘愿了。
赵婕妤捧着茶盏坐在昭阳宫中,听着徐容华前来与秦昭仪絮叨:「姐姐,不是做妹妹的小心眼,不容人,实在是这事太令人生恼。陈宝林算得什么呢,也能在上旬月里接驾?陛下起这心思,莫不是要在上等妃位里给她一份不成?」
秦昭仪从听闻消息以来,心里也十分诧异,依着君王往日作风和分寸,万不会乱了侍寝的规矩。
那一回徐容华使苦肉计想在下旬月里留住君王,不也没能成吗?
想不到那个陈宝林,平日里看着无声无息的,背里倒是个邀宠的高手。
只是这样酸溜溜的话,徐容华能说得,她却不能,便劝解着徐容华道:「大家都是姐妹,何必在这事上生了嫌隙?陛下去谁那里,也不是我等能左右的,倘或陈宝林真晋了位分,咱们还得给她贺一贺呢。」
「哟,昭仪姐姐可真大方!」
赵婕妤的茶盏捧不下去了,见过装模作样的,没见过这么装模作样的,要她给陈宝林庆贺,那不是打她的脸吗?
陈宝林什么出身,她们这几个人又是什么出身,凭什么一个七品小官的女儿也能和她们平起平坐?
「要我说,昭仪姐姐你现在可是六宫之首位,皇后娘娘不在,你就是位同副后,宫里头该管的还是要管,若不然,大家都没了规矩,长此以往,不都乱了套了吗?」
她管?她怎么管?人人都道她是六宫首位,可事到如今,君王连句准话儿都没有。
以往太后娘娘在,便是太后管理着六宫,现下太后仙去,陛下只说一切照旧,又未曾说让她协理。
再说内侍省的内侍监吴兴,那可是在先帝跟前就红透了的人,行事最稳妥不过,有他在,还能有旁人什么事呢?
她要管,也得师出有名才行。
何况,别以为她不知道赵婕妤和徐容华打的什么主意,不就是缩在后头拿她当出头鸟吗?
她要是管得好了,大家受益。要是管得不好,触了君王霉头,倒霉的还不是她自己个儿?
由是,秦昭仪只管端坐着,横竖那陈宝林再怎么晋位,也不可能越过她去。
除非陛下被鬼迷了心窍,越过她,封陈宝林做皇后。
说到皇后嘛,她倒是想起来:「那个……秋宫人,如今是否还在艺林轩?」
赵婕妤细长冷艳的眉眼一眨,也想起来:「没听说她去了别处。」
这就奇怪了,长孙秋水在艺林轩,陛下怎的还会去宠幸陈宝林?
难道是……
赵婕妤轻咬着朱唇,任是徐容华迟钝,这会子也听出一些猫腻来:「我说陈宝林怎会那么好心把她留在身边,还当她是真的顾念旧情,原来她打的是别的算盘。」
陛下厌恶废后是阖宫上下皆知的事情,当初人人都对长孙秋水避之唯恐不及,偏陈宝林一个人赶上前去,她们还以为她是痴傻了,想不到人家大智若愚。
陛下既是厌恶长孙秋水,那么故意要在她面前宠幸了陈宝林,以此报复她,也在情理之中。
这般说来,是她们当初看走眼了。
徐容华心下难平,那回她借着金华台上江都王妃闹事故意邀宠不成,事情传扬出去,她都快羞死了,然则彼时大家都以为是陛下不愿破了侍寝规矩,是以倒都没有说什么。
哪知这才过去几日呢,转眼陛下就在上旬月驾临末等妃的住处了,这不是明摆着让她成为六宫笑柄吗?
她恨恨不已,待告别了秦昭仪和赵婕妤,冷不丁在门口遇见陈宝林过来请安,一时难忍,不禁向她道:「陈宝林,闻说你宫里头有个绣工极好的宫人,正巧我这里有几样东西要绣些花样,嫌婢子们手脚笨,便借你的宫人一用如何?」
陈宝林焉能不知她的意图,中宫之主不过是一时沦落至此,竟还真把人家当成奴婢了,想要秋水去她宫里,也得看她愿不愿意,便屈一屈膝,不卑不亢地拒绝了回去:「请容华娘娘见谅,妾宫中只有那么三两人可供使唤,实在调不出人来去给姐姐。再则,秋宫人前次端茶倒水不小心伤了手背,这些日子都在屋里将养呢,只怕做不成什么绣活了。」
「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