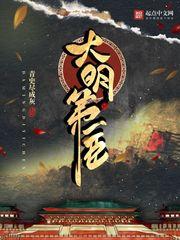笔下文学>魔女衣服素材 > 第331章(第1页)
第331章(第1页)
>
衣身眯眼细看,便见一弯虹桥跨在一峰一云之间。翠峰白云间,有仙鹤展翅翱翔,清唳在山谷中传来阵阵回声。三层的楼阁高居虹桥正中,雕栏画栋,云雾缭绕,恍若仙境。
衣身看了好一会儿,转过头往另一个方向望去。在那高崖之上,孤峰之巅,一栋简陋的石屋是那么刺眼。
苏长生在戒堂受罚,衣身在青炉峰上养伤,而同时,天阙宗的大佬们也没闲着。
此次秘境历练,损失了七八名弟子,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凡间日益繁华,肯秉心修行的人越来越少,培养一名筑基弟子不易啊!掌宗免不了要安慰一二痛失徒弟的各峰长老们。转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才歇下来,“苏长生勾结魔女”的流言又传得沸沸扬扬,便是在天阙宗里,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屁股还没坐热的掌宗紧握双拳,额头青筋突突直跳。
有关苏长生是如何与衣身在秘境相遇,又是如何相伴而行,以及如何救人等等,长老们皆自秘境返回的弟子口中了解得清清楚楚。便苏长生本人,也被掌宗、掌戒长老以及师父银山长老,轮番来了数次三堂会审。
苏长生自然坦坦荡荡,将他与衣身如何相识等等都交待了,包括神心果之事。当然,他也不是特别老实,说了七成,瞒了三成,譬如,夜闯明珠岛。明珠岛是东海大枭陆上龙王的地盘,他本能地认为隐瞒这一段经历可以保护衣身。而至于其它的,诸多细节也只一语带过,不必详述。
天阙宗自开宗立派以来,已近万年。而始终居于“五宗八门”之首,自然与其门规森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位大佬合计了又合计,反复斟酌推敲,并未发现苏长生的讲述中有何漏洞。而银山长老更是相信爱徒绝不会交结歹人。掌戒长老虽然严苛,却并不迂腐。他皱眉道:“依着长生的说法,那姑娘行事作派都不错。我瞅着那姑娘眸光清亮,眉目端正,也不像个魔女。可流言凿凿,只有你我知晓有什么用?总得给外人一个明白的说法。”
掌宗捋了捋雪白的长须,叹道:“正是这话。勾结魔女,这罪名可不小啊!”他嘿嘿冷笑两声,“倒不知是哪个想要掀起波澜?”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管是天阙宗还是苏长生,从未少过遭人嫉恨。不被人妒是庸才——掌宗虽觉得烦躁,却也无惧。
银山长老思忖片刻,道:“若要给个明白说法,就免不了说清楚那姑娘的来历。长生语焉不详,只怕他也知之甚少。看来,得与那姑娘见一面了。”
一抬头,见掌宗和掌戒齐齐望向自己,银山长老胸脯一挺,“人在我的青炉峰上,自然是我去。”
自打衣身苏醒过来后,她既没见过苏长生,更没见过银山长老。况且,为尊者讳,袁招招、钟石头等人在与她聊天时,也极少提及师尊银山长老。故而,当袁招招一脸恭敬地将个糟老头子引入院中时,衣身还在发蒙。
当晓得眼前这位就是脚下这座山峰的真正主人时,衣身顿时肃然起敬,却又忍不住偷眼打量,然后暗自叹息:唉,大叔拜了这么个糟老头子当师父,委实不易啊!
银山长老自然不晓得衣身此刻真在腹诽自己。他自以为潇洒地捋着稀稀拉拉的短须,面露自以为慈祥的笑容,却不知在衣身看来,愈发显得猥琐。
袁招招也觉得师父今儿这作态有些古怪,却又摸不着头脑,只得硬着头皮打哈哈。哈哈打了没两句,就被银山长老拦住了:“废话少说。为师此来,是看看长生带回来的姑娘是何许人。”
袁招招不敢再说话。衣身却笑而应道:“长老,您看我像是魔女吗?”
因着衣身赠与苏长生一枚神心果,银山长老对她印象不错。此刻,见这姑娘说话直率又大胆,愈发觉得有趣,索性敞开了说明话,“长生好端端一孩子,却被你带坏了名声。你说,你该当何罪?”
“您是来兴师问罪的吗?”衣身靠在背枕上,面无惧色,“只可惜您问错了人。”
“此话怎讲?”
“有罪的是散播谣言的人,却不是我。您不去抓那胡说八道的家伙,却来问我,难道不是问错了人?”
银山长老俯下身,直勾勾地盯着衣身,“是不是胡说八道,还要看你究竟是何人?或许,你就是魔女呢?”
此言一出,一旁的袁招招惊得花容失色。
衣身不露声色地瞅了她一眼,笑眯眯道:“您说我是魔女,我却是不认的。您这么一大把年纪,又是大叔尊敬的师父,必是德高望重的老神仙,想来不会信口开河,总归是有证据吧?那么,老神仙,您认为我是魔女的证据是什么呢?”
衣身这番话,连嘲带讽,可谓大胆至极。银山长老的脸顿时拉长了三尺,面沉似水。袁招招更是骇得面色苍白,身子止不住地微微颤抖起来。
第一百九十九章
虽说青炉峰的弟子们都是由大师兄苏长生代师收徒,却并不意味着银山长老在诸弟子心目的地位不如苏长生。
银山长老的脾性有些古怪,说好听点儿是洒脱,说不好听就是任性,行事作派,可不像个名门正派出身的规矩人,很是不拘一格。遇上这样的师父,于诸弟子而言,幸也不幸。
幸运的是,银山长老收徒不讲究出身,管他是杂役还是妖怪,合了眼缘便大手一挥,纳入门下,平素里也不怎么管束,讲究的就是一个“散养”。不幸的事,师父的脾气就跟六月天似的,好不好的,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说不得啥时候,师父看谁不顺眼了,这孩子就该倒霉了。